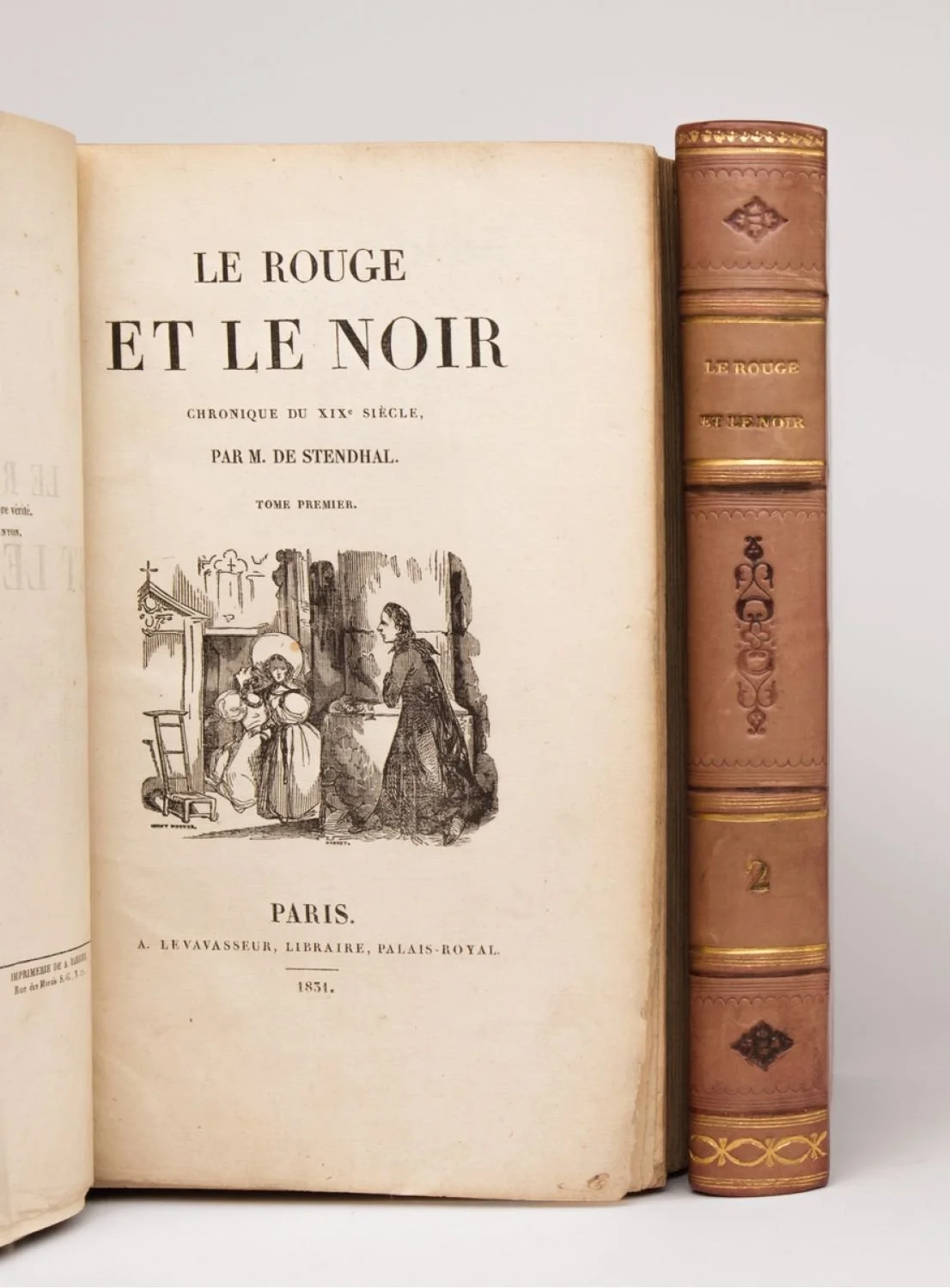Scorpiris Schemata 蝎鹫尾图式 第二十章 影子的侧写
第二十章
A Study of Shadows 影子的侧写
主要坐标: 拉神神殿,赫利奥波利斯,埃及,33 BC. Temple of Ra, Heliopolis, Egypt, 33 BC.罗敏特猎场,东北波兰,1733。Rominter Heide, Northeastern Poland, 1733.
明斯克,波利联邦,1753. Minsk downtown,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1753.
建议配乐: 第一幕:“Smoke (Theremin Instrumental)”, by Armen Ra.
第二幕:“Void”, a piano composition by Lucas King.
第三幕: “Verklarte Nacht, Op.4,” by Arnold Sschoenberg.
...Ιρις...
桑德兰看着异教神殿燃烧崩塌,也许潜意识里他知道这是他亲手造成的。
他简短地端详了一下那只正在以可见的速度逐渐腐败变形的,残缺不全的鹰隼遗骸。或许是出于过往的职业素养,桑德兰半心半意地辨认出这个Praeterita-vita (往生)被取巧地反向逆转了防护魔咒。它甚至都不能维持鹰形,光照下的影子是畸形的人形,从倾斜的头冠轮廓可以看出他穿着王室的礼服。[1]它失真地低空悬停在神殿的入口处,已经死了,上翻着蜷曲成一团,仍然在不住痉挛抽搐。仿佛在警示来往过客:Lasciate ogne speranza, voi ch’intrate (入此门者,需摒弃一切希望)。
傍晚时刻的橙色基调将火光与烟雾照成暖色,左手右手边竖立着两座尖利的棱柱形黑塔,塔前的狮身人面已经被粉碎咒破坏得面目不清。两排对称的石阶顺延而下未干的血迹,酱红色藤蔓般顺着立柱旋绕而上,在顶端汇集成刻意而散乱不堪的符文,让人无法准确辨识出使用的语言。
他知道自己不该进去,并非是出于猎奇或是好奇。但他依然被某种致命的吸引力牵引着,缓缓步入了那个岌岌可危的开放式建筑。
到处都是火,和被火烧着的活人和死人。地狱却无法真正触及他。一片狼藉,空气中弥散着肉体烧焦的糊味。祭司在地上,与卫兵,信徒与神殿舞伎享受同一个命运。令人反胃。
他下意识地绕过盘旋在地面上的血迹,走过散落一地的细沙,无首的石像,以及掉落在地上的鹰头。来人的做工滴水不漏,连走廊用于祭祀仪式加持的荷鲁斯之眼纹饰都没有放过。两侧的壁画上溅满了血点,精巧的蛇形太阳头冠被腐化成了象征日食的黑色。贡品,弦乐器乐器混着几支被折断的魔杖散落一地。火烛熄灭。
不出所料,站在主殿正中的唯一生还走出了用仇人鲜血化成的一对同心圆环,摘下了外层斗篷兜帽,桑德兰看到了他自己。
他轻轻地笑了,左眼或许是被火光染成诡异的金绿,旁边却流着一滴泪。
“我们好了?” 桑德兰看到他在和不在场者低语,“不管如此。就这样吧......”
他垂头站了半晌,决定继续下去,将以一个诡异姿势扭曲在地上的盛装祭司用力掰直,翻转过来,抽出了腰间的匕首。几乎是条件反射地,精准地从左胸腔刺入,对称两刀顺延划下,刀刃上翘,它的胸腔从中间翻开。
他将大祭司的脏器逐个掏出来,整齐地分类,摆了一地。
鲜血淋漓的心脏被留到最后取出来,他用匕首尖在中间刻下,漫不经心地,“Σ for Σεβᾰστός (S for Seweryn).”[2]
几声不连贯的嘶嘶声打断了这个亲密的时刻。
“安静。” 他听见他自己轻声说。一阵大概是抗议的急促嘶嘶声过后,神殿重归于平静。这种半自愿的共生状态,合作虽说并不一直愉快,经过反复磨合勉强算是押得过去。他找到了它,或者说,它选中了他。对于它的动机他并不真正明了,想来也不会有这一天。不过这不重要。
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总算感到了一瞬间的平淡的满足。他被他们不可原谅的行径强迫着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仅仅用于达成目的工具,并且心甘情愿。当他亲眼目睹赛维林倒下去时,以为他属于人类的情感已经麻木了。创口却好像将他也连带着击中,反复烧灼,持续不休。或许对于逝者的回忆比起作为活人的仇恨更加具有穿透力。至少现在,脑海中的絮絮低语总算停下来了。就算短短一刻也好。
他曾经以为在此之后就可以翻过这一章,继续走下去。看来还是过于天真了。
桑德兰看到自己抬头,低矮的天顶上显现出一片不断闪回的星群,蝗虫般无序地盘旋坠落,转眼又化为一片漆黑而阴沉的海面,浑浊的波浪席卷着像魔物的獠牙。辨识不清自己究竟是在天顶下还是黑水中。他眨了眨眼将渗出的一点水光含住,忍不住掠过一个悲哀的冷笑。
他站在祭台上,与身周被毁坏的雕像融为一体,俯视着他的杰作。他等这一天已经太久了。说真的,他没感觉到什么预期的畅快,安宁,或是别的什么东西。理性上他或许可以欣赏这个画面。缺失的依然缺失,好像被虫咬噬的空洞,有了一点征兆就不可收拾。它缓慢地,势不可挡地将他腐蚀。
或许这样也好。
或许本该就是这样。
桑德兰认为他有一瞬间想躬下身来,用双臂拥住自己。当然他不会真的这么做。他站起身,将匕首收鞘,做了个手势将火熄灭。桑德兰看着自己面无表情地擦肩而过,快步离去。
他和他的影子重合了,在白日的火光中。无辜者,罪犯,罪有应得者,祭品,祭司,黑巫师。他永远无法洗去手上沾染的鲜血。尽管他圣力下的亡魂或是他们的子裔杀人如麻,且毫无悔意。
他没有回头,却照旧变成了石像。[3]
...Ιρις...
又是森林与旷野的边界。我对这种模糊又清晰的地方有着说不清楚的感觉。凉风划过耳鬓,浑然不觉。
这次仅仅是路过。一面好奇的漠然。对于这些圣经派新教徒来说,头号反基督的是教皇,其次才是血族巫师之类的黑暗生物。
我在半枯萎的针叶树前坐了下来,它似乎被闪电击中,半面焦黑,不受欢迎的似曾相识。这个意象反复出现,如同边境的分界石,已经让人厌倦了。
母鹿。我跟著她到了溪流。她.....受了伤,大概是被攻击了。
仁慈而迅速的,你追踪了它?
看到她跌撞著踱过,最后精疲力竭地前蹄弯折,跪了下来。我举起了猎枪。知道最后狼会找到她。我看到了她已经被獠牙撕裂,暴尸在外的景象。
你失望于浪费。
取了他们需要的,将其他部分留了下来。狼也需要进食。
是的,它们需要。狼是群居动物,它们一起狩猎。
他们也单独作业。桑德兰指出。
当必要时。
两只并不称得上群居。
算是同居?就算只是在臆想中,希拉也一日往日。它抖了抖手腕将“希拉的剑”收起来,忍住不继续推进。啊,一个充满同情的猎人?狼群里的羊----不,狐狸。它确定这个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狩猎。一个可以共同完成的,疯狂的乐趣。允许你自己享受其中。与我一起。在我眼前。在我身中。
记得你曾经狩猎黑巫师的时候么?
其实我隐约知道,我当时并不只在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必要的......额外伤害。桑德兰承认,应该在更多的时间尽量与自己诚实以对。
我从未更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活著,肃清时,与它一起时。
抗拒我,抗拒自己?
背叛你,背叛自己?我如何分清我需要的,我想要的与你想要的?
它们不能是同一个东西么?
我侧头,不予理会这个多余的问题。现实中希拉从不多话。
也就是片刻后,一只幼鹿姗姗来迟。桑德兰闭上了眼。
依然可以听到断续的鸣啼。以及背后什么其他的,模棱两可的语句。
我重新举起了猎枪,却扣不下扳机。
我要是你。这时希拉瞬移到了我身后,话只说了上半句。它离得非常近,可以清晰辨识出鹫尾和没药基调的分层,甚至将手覆在了我的手上一同握住了枪柄。反正你我都知道,它凭自己也活不下去。
我不是你。
希拉没有回话,但我从它眼中理解了下句的大意:你现在可以这么认为。
...Ιρις...
或许他现在可以这么认为,桑德兰眨了眨眼。
他再次醒来,发现自己在中洲一条昏暗的街区巷尾。天色显示很是平常的一天,地上整齐地按照身高肤色摆着一横排失血而亡的人类尸体。
受害人衣衫褴褛但衣着整齐,根据时间顺序排列成一行,从略显尸斑到新鲜的刚死了不久。他们和她们被摆成双手放平的安详姿势,好像睡着了一样。他们脸上如同盖上了一层面具,没有忧伤,痛苦甚至惊惧。
或许唯一证明先前单方面屠杀的是静态的画面。
忽然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一切都笼罩在一片发红的黑暗中。他再次眨了眨眼,由衷期望这属于他似是而非,虚实交错的幻觉。这几乎是立刻就被证实是不切实际的。
他久久凝视着摊开的,一尘不染的手。记忆空白,不知对此应该是庆幸还是骇然。
他挣扎着蹒跚到近前,强迫自己注视着他举动的后果。桑德兰拨开右数第二具女尸凌乱的枯黄长发,低头仔细端详着她颈动脉上一对咬痕。两个低陷下去的出血点,外围已经开始晕起一圈淤青紫色。不可想象,凑上前将尖牙陷下去,舌尖品尝鲜活的血流是什么样的感受。他甚至无法推断,他们是如何被牵引或是转移到此处的。一切似乎结束得非常快,四周完全没有挣扎的痕迹。
他研究着它们,像是观察着什么僵冷的无机物体。头又开始炸裂似的疼起来,他的脸色苍白,全身控制不住地轻轻颤抖。那一向宁静温和的脸由于某种悲哀扭曲成了无法形容的表情。
最后一具躯体孱弱的小臂上伤痕累累,有些鞭痕与烟头的痕迹生前已经开始溃烂。他双眼失去焦距,缓缓单膝跪下,虔诚地伸手给那个无法起死回生的孩子合上了眼,将外套脱下来盖在了他的身上。
桑德兰的手臂几乎丧失了活动,嗓子业已哽咽着不再能发出声音,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力。他失神地后背靠向青灰色砖墙,无法忍受用十一具尸体的死寂填充寂静。
从视觉死角走进一个凭空出现的窄小身影,当桑德兰终于辨认清时,他甚至要笑出声来了。是该这样。她穿着她生前最钟意的那件她执拗着要女仆缝补几次舍不得扔的白色晨礼服,裙摆上全是血。爱莉冷冷地从黑暗中看着他,手中捧着一只清理干净的头骨。她青紫的嘴唇并没有动,上扬成一个刻意的,礼节性的弧度。
桑德兰却听见他耳边传来重复不断的低语声。绝望而死吧。[4]愿你绝望而死。爱莉伸出幼嫩的小手把玩着骷髅左眼中插着的一支枯萎的法国玫瑰。你会因为你的罪行在绝望中死去。他尽力用双手堵住耳朵。继续做你的噩梦吧。她捻指掐住尖刺将花枝折断。无济于事。噩梦属于你。绛红的花瓣掉落到地面上,溶化成了更多的血迹。唯有绝望是属于你的。她放开双手,任由骷髅垂直摔落。他眼前猩红的雾气更深了。
希拉还是来迟了,即使是探查了它们之间由血源联结而成的纽带。它快速扫视周遭解析目前的状况,比它想象的稍微好些,猎物被有效率地集中赶进了隐蔽区域,脖颈间的齿痕干净利落。一些漂亮的尸体。看来桑德兰属于艺术家一挂的,而并非屠夫。
尽管对于错过了教导它的幼崽猎食,它略微有些不满。
不然,桑德兰或许做的太过分了。出于某种不成文的规定,它们一般并不猎杀幼崽。不过这并不怪他。
希拉弯下身,将厚重的黑斗篷解下来覆在了它的男孩的身上,紧紧用双臂围住了他。
“你事先知道。” 耳后传来细不可闻的自嘲。
“不。” 我不知道。没有血族做过这种尝试。长期用自己的血液,自己力量的来源供给他人。
希拉合住双眼低声在完全无法做出任何回应的血族耳边反复道,“算在我身上,算在我身上。”
它看到桑德兰嫣红的嘴唇动了动,现在什么也不用说了。
.לַעֲזָאזֵל 希拉低声咒骂了一声,小心地将失去反应的男孩托起来,像是拥着什么易碎的瓷器。虽然面色终于因为节食中断变得有些红润了,它并不喜欢这样的桑德兰。[5].בן נעוות המרדות
它直接打开炼金术师通道,走捷径传送回庄园地下,将桑德兰轻轻掼到了四柱床上,扯下用来固定的黑色绸带放下了厚重的帷幔。
想来它现在大概是与他共处一室的最后人选,希拉起身准备去书房,叫它副官尽量在茨维坦·茨维坦诺夫那个社会党的败类发现他封地上发生了什么以前去将尸体运到斯维斯拉奇河里扔掉。转身时却被挽留住外袍袖口。它不由叹了口气,一个无声的邀请。
作者注:关于第三幕的特写部分,调取了几份关于动物袭击的尸检报告大概看了一下作为参考,像野狼和大猫。由于串行了,估计鉴定部分仍然有不符的,欢迎查漏补缺。
[1] XXXIII王朝时期拉神Re和阿蒙Amun合并了,所以傍晚时间一般用Amun的形象示人。埃及体系的诸多神灵常常以政治风俗等等原因合体。Karen Bryson, “Re: Sun King of the Egyptian Gods,” American Research Centre in Egypt, online, accessed 2019.)
[2] 向托马斯·哈里斯的《少年汉尼拔》中经典一幕致敬。M for Misha.
[3] 至于桑德兰是引用了索多玛妇人的还是欧律狄斯的典故,还是请诸君自行选择吧。
[4] “Despair and die.”出自威廉的《理查德三世》,5.3.126.
[5] (ft. “damn it,” “Ben Naavat Hamardut, son of a rebellious indiscretion.” 希伯来文脏话非常罕见, 多数是阿拉伯文, 意第绪语等等的派生。第二个是圣经中蜿蜒曲折的用来咒骂的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