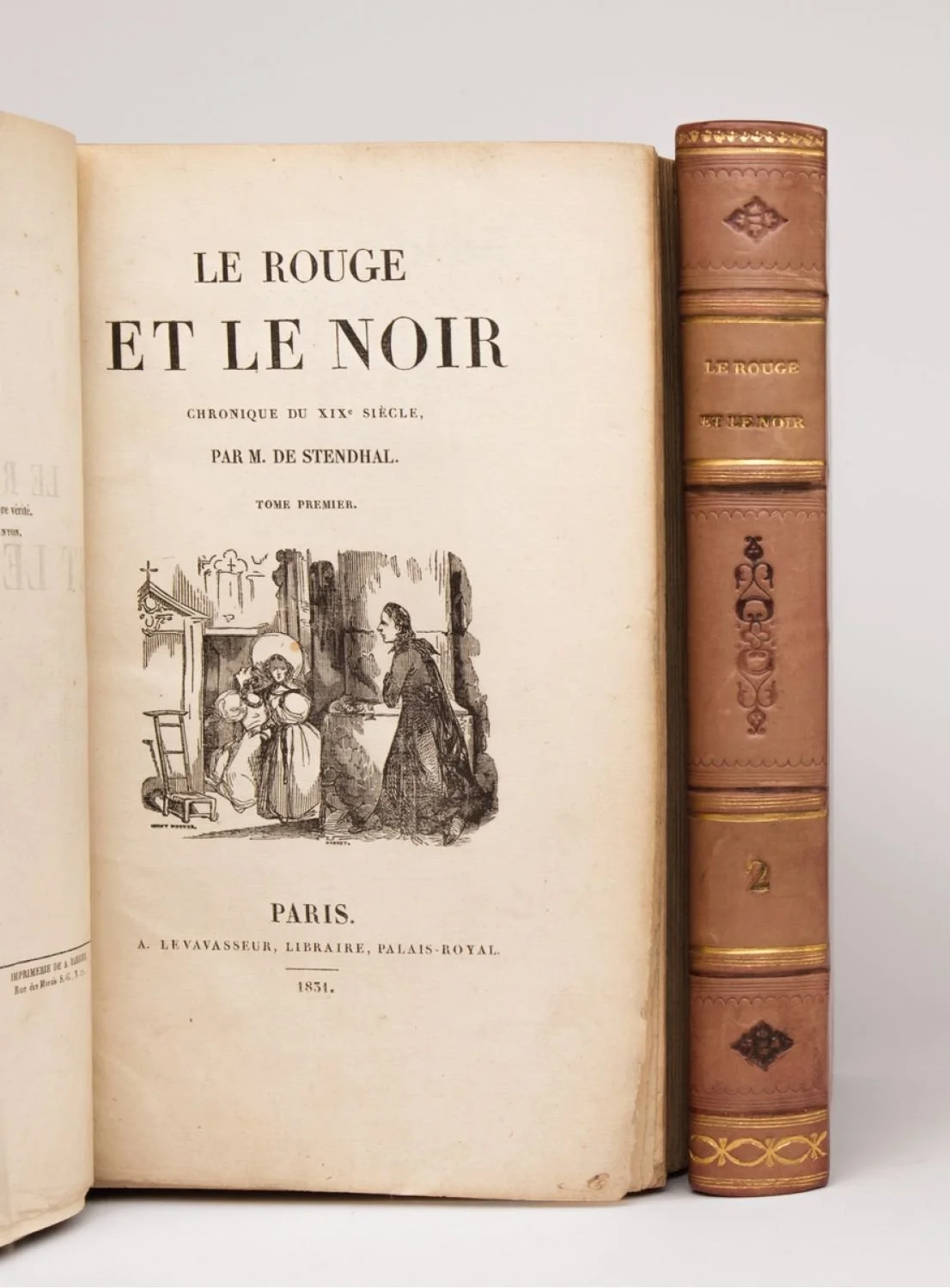Scorpiris Schemata 蝎鹫尾图式 第二十六章 悬崖边的风
第二十六章
Wind among Wind 悬崖边的风
主要坐标: 月落城北翼,希拉·勒托里亚II的深红庄园,主人房,1756。
Moonlit City, Northern Laetorii Territory, Crimson Hill of Lord Zillah Laetoria II, Master room.
月落城,议事厅二层,勒托里亚法院图书馆,1754。
Moonlit City, Basilica, the Law Library of Laetoria,1754.
中洲,波利邦联,勒托里亚亲王封地, 一个村落,1756。
Mittleland,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Laetorrii Principalities, a Shtetl,1756.
建议配乐: 第一幕 Elena Kats-Chernin et al, “Roses in a Box”.
第二幕 Paolo Buonvino, “The Truth”.
第三幕 Lucas King, “Sociopath”.
...Ιρις...
桑德兰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他的棺材里。他想假如不是他的记忆出现了隔断,那么一定是时间出了什么不可解决的问题。
目前能见度为零的黑暗给他带来一种安全感,这里时光匀速流动,静谧地让他几乎听不到远方的血流,或者未曾停歇的流沙。不同于其他人梦醒之后,竭力想抓住一丝一缕的片段,他一动不动地将碎片搁置着,甚至连将它们收回盒子里的余力都失去了。尽管如此,它们在眼前划过之后,有些东西依然在持续颤动。虽然渐弱下去了,假如仔细观测,依然有所感觉。
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不可以,直到他听到外面有人敲了敲大理石盖子。
他将身子蜷缩得更紧了。
“请你出来一下。” 希拉礼貌地回答。
“有什么事?”
“我需要你出来一下。” 沟通很快变成了命令。他叹了口气,按机关掀开了棺盖,立刻被外面稍微亮一点的,被烛光点燃的黑暗刺激得眨了眨眼。
桑德兰像个听话的提线木偶一样直起身,试图转移到衣帽间拉铃叫人更衣,最大程度地降低他与它单独相处的时间,却被率先拉住了胳膊。“这么着急?”
不然您说呢。他低头瞧着希拉手腕上反复烧灼又愈合的伤痕,平常被手镯挡着,偶尔暴露在空气中,形容狰狞。
希拉也不急了,索性坐在了它的棺沿上,像是在等他从过往的梦境中挣脱出来,或是说重新沉落。
凌乱的案头熠熠的烛火,掩饰了他们之间复杂而纯粹的沉默。
桑德兰眨了眨眼意在再次确认,眼前的血族消瘦的身影边缘模糊起来,转而又变得异常清晰。一个扭曲的肖像。
这是希拉么,哪一个才是希拉?(好吧,这是希拉算了)。[MOU1]
一个浅浅的笑。桑德兰轻轻握住它的手腕,露出尖牙哺了上去。
希拉显示出满意的样子,它伸手拂过他的脸颊,强调了这种互动的仪式感——一个久别的仪式。他即刻尝到了血源释放出来辛辣的甜味,与他血管里流动的相似而不同。
下一秒钟,他与它的位置似乎调换了。他将头枕在它膝间,盘桓着抬身交出脖颈,希拉格外温柔地看着他,将尖齿刺入青蓝色的脉络。不知是谁面色苍白沁着红润,在光线下几乎半透明,并不感觉到疼。肢体死了而血源清醒着。血液流失,又失而复得。
他有些受够了。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他却总是要被迫去吃……
他有了足够的板块,却拒绝将拼图拼起来。于是片刻它们又被打散了。四散在别处。
“好了桑德兰,你大可以想些别的。”它可以非常正确地说,对于它们来说,至关重要的,从来不是过去。但是鉴于说了和没说一样。
“您是不是想说:去过去寻找完好的瞬间?”片刻他就错开了,侧头避开目光,算是掩饰了恋恋不舍的犹疑。希拉脸上的阴影使他有些不安,就像突然幻听到过去熟记于心的乐曲,或者过去的香气似的。
“对,就是这个意思……完好的瞬间……”希拉注视着昏暗的装饰性彩窗。它的双眼红得发黑,像是下一秒钟就要渗出血来。它不会像他一样活在想象中,回忆和现实却几乎占有等同的比重。
烧痕上的伤口肉眼可见地愈合,很快就消失了痕迹。墙角和天花板的直角似乎划过一只漆黑的蛾子,或者蝙蝠。
他想了想,想说些什么。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却没什么好说的了。
希拉最后打破了沉默,“费安尼洛为你准备了什么,抽空去书房看一下。” 它站起来,转身走了。
好像它从来就没有来过。
烛光继续摇曳着,它会给他制造一种错觉,而错觉会轻而易举地使他沉沦。
...Ιρις...
深红庄园住着个幽灵。桑德兰终于在碰到了,还是在庄园之外。
他们从法院图书馆书架两边取到了同一本书。
”不好意思,女士优先。” 开口就是辛辣的讽刺,但他先松了手。长远来说,在勒托里亚法院里挡勒托里亚亲王配偶的道纯属浪费时间。
“先来者优先。” 察觉到没有恶意,桑德兰轻轻将部头推到了对方一边,笑着回了一口。
深居简出的门客竟然也接受了,他将德鲁索斯激情洋溢奋笔疾书,西蓝序的《再论所罗门扈从法II》手稿夹在胸前,抿嘴回了一声“谢了”。
桑德兰听出他的声音刻意压得很低,以致于有些喑哑。结合高领衬衫和宽松的学者外袍,他在迅速排除掉其他可能之后得出了一个不大可能的结论,他慢慢眨了眨眼。不过这不重要,他此时也没有什么立场去质疑他/她的选择。
“我似乎之前听说过您们……冯·克里特……” 梅策尔德陷入了短暂的沉思倒带,“啊,对了。那个愿意亲自上阵的阿德莱德侯爵。” 梅策尔德选了个不难听的说,他没义务恭维别人。
“这是比较少见的。”他也非常愿意不接受别人的恭维,那些口蜜腹剑的官话日积月累下去,就是那么回事。
“更少见的正站在我眼前啊,勒托里亚主教。” 他很愿意继续这个话题,三年前前信理会部长在冯克里特家的越权执法给罗马制造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烂摊子。为了避免隐性丑闻演化成显性灾难,那学者教皇居然将大绝罚令按下不发。也是魄力十足。
这也间接性地导致了教会法意义上说,在未确认死亡的情况下,桑德兰·冯·克里特依然保有主教头衔。
现在是冯·勒托里亚-克里特主教了。何尝不有趣。
桑德兰与梅策尔德是完全不同的人,而他们两个对这次会面都比较满意。梅策尔德鄙视傻子,而桑德兰也喜欢同聪明人过招。
桑德兰得出了一个较为准确的推论,梅策尔德是那么一类人,没有人可以与他们对时间,空间和事实的掌控能力相比肩。他的思维大概会看起来像个工厂的控制室。曾经被称为”天才”, 受到广泛的认可的那一类人。更有甚者会称呼他们为,没有国土和国界的无冕之王。
梅策尔德这类人对现实并不存在幻想,反而可以轻松地渡过每次权力激荡。他这种人在王权,共和国,或者独裁体系下都寥寥无几,供不应求。当桑德兰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仅仅被容忍时,梅策尔德属于那种不可取代的专家。希拉在建了个火车后很快地发现它无法将它启动起来。而梅策尔德这类专家就在财权,或者一些别的什么的盛情邀请下,零星出面示范如何推动手柄,如何启动蒸汽引擎。 不,对于当时三代血族篡权阴影还未消散的勒托里亚,可能要从修改和细化图纸开始。
比起婉转温和的手段,多方利益和少数派的权利,他们笃信纯粹的连贯性,不受干扰的持续运作和绝对的权力。毫无对未来的期望或者想象力,因为了解什么是可能的人不可能去将时间浪费在虚无缥缈的可能性和不可能上——而这是桑德兰自己的错误。
当桑德兰将梅策尔德定义为精准冷漠的机器时,梅策尔德认定桑德兰是个被信仰(他私以为是迷信)和道德绑架的理想主义白痴,好极了。
“说起来真是尴尬。” 他之前的身份如影随形地跟随着他来到了这里。威廉姆公爵和他的随从防他堪比普鲁士人防条顿骑士团的程度。假如宪法允许,他估计已经被弹劾数次了。他不作为是拒绝同化月落城社会,他稍有动作则是教廷势力企图干政。
以至于他到底在这里做什么,算是什么,他也不十分清楚了。就像一本书将开放式结尾仔细构造成了形容模糊的开放式,新的开端写了一半,却不想续写下去。
“希拉的塔楼里骸骨不止这一架。” 他名义上的哥哥略微修改了一下语意用词。他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不止这一架。” 桑德兰同意。假如他真的明白就好了。
...Ιρις...
他们坐在书房角落的茶桌前,落地窗翡翠蓝绿的帷幔并没有紧紧拉起来,窗户开着,只是盖了层随风微微浮动的纱帘。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将他一身淡蓝常礼服染成了湖蓝色。
桌上放置着热腾腾的红茶,他和管家都没有动。
“先前并没有接手过雾色山脉的事务,如果可以问一下,奥克斯是出自哪里?”这个问题他早就想问了,不管是教廷内部的文献,还是他间接接触到的零联盟未来得及销毁的档案,都对此讳莫如深。虽然现在看来已经无关紧要。
费安尼洛拖住下巴想了想,这个动作在他身上出奇地和谐,“大概是一种光之神科米提斯堕落的信徒。”他措辞非常小心。
桑德兰等着下文,他有一种这不会很美好的预感。
“或者说,是精灵被人体炼金术失败的产物。”在科米提斯与莫瑞亚用尽最后的能量同归于尽之后,这些曾经的诸多隐秘禁忌也成了过去式。费安尼洛感觉到血族眼中闪过了一丝二手哀伤。这是一个好孩子。
“言归正传,虽然体系不同,河谷使用的光系法术与圣光依然有很大程度的重合。”他站起身,从那一摞排列整齐的文献中抽出来需要的那本,“虽然被剥夺了科米提斯的荣光,现在我还可以和你讨论一下理论。”
桑德兰向前欠身接过翻开的那页,竟然是娟秀的手写德语。像是察觉了他的疑惑,副官解释,“我闲暇之际的爱好,总觉得有冲动将这些极易遗落的东西用通用语记录下来。”他的翻译。
“针叶之箭的输出方式和光羽术很相似。”他继续读着,不觉说出了他的观察。
费安尼洛笑着点头,“精灵们需要就地取材用他们用得上的。” 他接着报了几个页码请桑德兰查看,“据我的不完全了解,光系大多强调治疗、辅助和防御,这一点我们所称为的光元素和圣力都一样。”例如复原术对应治愈术,梵雅的屏障与纯白之盾很相似,而桑德兰推论这并不止于中级咒文。
他思虑已久的课题,居然在多年以后被这样解了。这曾经或许会让他激动欣喜,现在却也喜悦不起来。
被雾色山脉明面上装作不存在的继承人大概是在某些血族旁敲侧击,隐隐施压下才“主动地”将湖区精灵的内部资料取出来的。不仅如此,确切地说是倾囊相授。
他知道他应该表示感激,可是。
“βέλος του φύλλου (针叶之箭)。” 他召唤了一片叶子,尝试着操纵它打着旋儿,落到了茶里。针叶和茶叶混迹一团,始终格格不入。
他的临时导师抽出了另一本薄薄的手记,“至于攻击法术呢,在约书亚的信徒们选择召唤各个等级的天使化身的时候,精灵们则偏向组合使用其他元素,或者使用弓箭。”
“我此前使用的加百列与拉斐尔甚至在……之后也没有撤掉他们赋予的权限。”单单是圣力的天赋就让他很无法理解,至于需要借用天使长神识的高阶召唤神圣降临一类就更加令人困惑。
“说不定那两位偏爱您。”费安尼洛打趣道,“现阶段先生怀疑勒托里亚的天赋放大的是你对光元素的感知,所以在圣光体系的效果增幅的情况下,不妨试试精灵的光系法术。”
“受宠若惊,然而这个…….”各族不会避嫌么。
“我认为被辛苦推敲演算出来的知识就是用来共享和使用的。”虽然雾色山脉绝大多数老派人目前并不这么认为。前精灵轻描淡写过了一个十分严肃又十分浪费脑力的问题,他像那摞书做了个邀请的手势,“鉴于实践看来不是问题,我先选了几本关于光元素理论和输出方式的论述。”桑德兰谢过收下,管家又略带抱歉地说,“有些是比较早的纪翻的,我认为您识得拉丁和希语?”
“拜家母所赐。”他略带怀念地说。
“那一定是位很可敬的独立的女性。”费安尼洛真诚地说,“那目前就先这样,如果遇到什么疑问,请务必不要迟疑来联系我。”他翻开怀表形的通讯水晶看了一眼,“先生领地上阿什肯纳兹与本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更胜从前黑森林边境林谷与湖区精灵共存的情况。”
“希拉领地上有希伯来人?”桑德兰佯装惊讶地问。
“都是这样,还能去哪儿呢。“ 他叹了口气,两人站起身后微微互行了个礼, “很高兴终于认识了您,Consort。”
感觉这个称呼无法被更改了,他并没有继续纠结,“我也一样。”
...Ιρις...
理解了核心理论,对于一个主教级圣光使用者来说,练习同系咒文并不需要循序渐进。指导着过了几个咒语之后,桑德兰和费安尼洛谈得平静安然,管家接到传讯蝙蝠的消息,道歉说需要紧急出去一下。
“领区出了什么事么?” 虽然桑德兰不知道他应不应该问。
他面色有些为难,“或许应该这样说,您不会想知道的。”
他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却不愿再承担不知情的特权了,“那么愿闻其详。”
他们一前一后从传送口出去,他深吸了一口夹杂着烧焦了的血味的冷空气。
针尖树和深夜的风。外边的景致让他产生出一种漠然的心态。他们真的也处在这个景致中么?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茨维坦诺夫的血系到希拉封地上,不多不少杀了十一个天主教徒。基于某种礼尚往来的原则,假如不意图使事件升级,深红庄园现阶段无法做什么。
确切地说,死者是被从案发地点移动过来的。这么做所强调的当然是一个微妙之别。
桑德兰垂下头,刘海颓然垂下一缕,刺入眼睛里,眼睛却一眨不眨,理所当然地——端详着一排整齐划一的死尸。
要是早些时候,桑德兰可能会这样想:他要怎么做,才能让这成为对的?
如果选取原先的原则,他接受个人对自身选择所带来的责任。这是说,限制在严格依照正当执行事先确立好的行为准则,并且自身也接受不可避免的有效结果的先决条件下;这是天主教的解决方案。[1]
可是规则改变了,甚至可以说发生了反转。这让他不免有些茫然若失起来。现在他面对这个景象算是无动于衷的。
也许一直以来就是这个样子,人们每天都在死去……月光将他们脸上涂上了一层石灰色。他们真的存在过么?
他清晰地记得,他不曾记得了。
可是就算这样,问题也不会不等他自行解决,特别是在他自主选择站在这儿的情况下。他若无其事地说,“请向每位死者亲属发放抚恤金和安葬费,记在我的账上。”
费安尼洛也不说话,等着他决定靠在一边作为承担全部责任的弃子的下场。那个刚刚处决式解决了一群信徒的社会党血系安详地闭目养神,好像对自己的命运全不关心。
在别家亲王直属封地上越权了的,一般处以火刑。何况他还越了级。“领主事务繁忙,害得您白走一场。恕不相送了。”
陌生血族忽然睁开眼,带着奇怪的微笑说,“您确定吗,先生?”
他不再回答,开始和管家系统化地清点起伤亡来。
[1] Leszek Kolakowski, “The Priest and the Jester (1962)”, trans. Paul Mayewski, on Dissent Digital Database,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