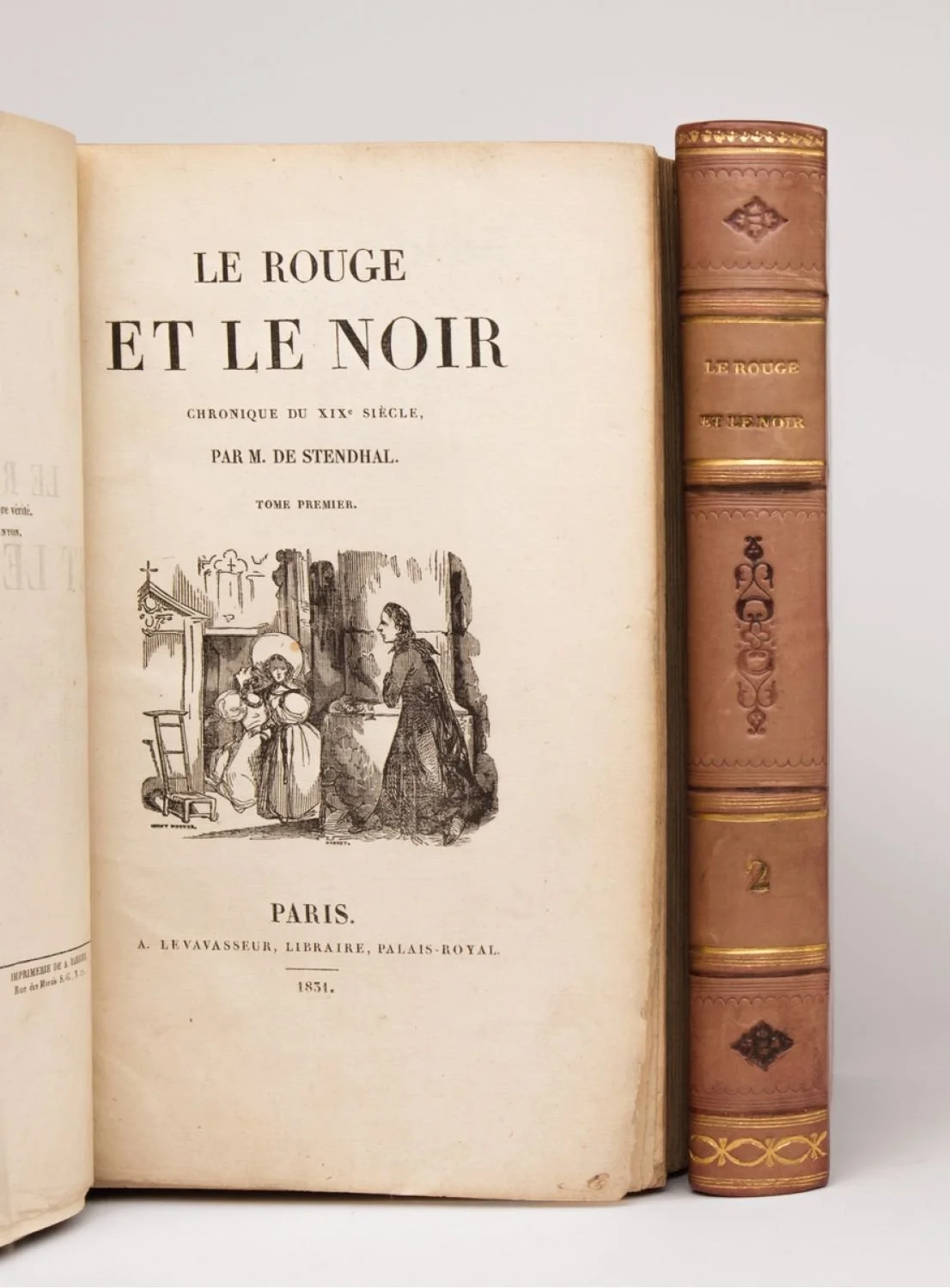Scorpiris Schemata 蝎鹫尾图式 第二十一章 F小调双重镜像
第二十一章
Mirror Image in F Minor F小调双重镜像
主要坐标 夏宫,维也纳,奥地利,1753. Schonbrunn Palace, Wien, Austria, 1753.
圣瓦伦丁皇家学院,伦敦近郊,大英帝国,1753. St. Valentine Royal Academy, London, British Empire, 1753.
建议配乐: 第一幕:“Piano Concerto No.2 in F Minor, Op 21: I. Maestoso. “ By Frederic Chopin
第二幕:“Piano Concerto No.2 in F Minor, Op. 21: II. Larghetto. “ By Frederic Chopin.
...Ιρις...
夏宫。就西里西亚问题短暂的交谈。当然愉快,但不出所料还是搁浅了。
他上次来夏宫时还是个孩子,那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阿德莱德好整以暇地在一旁等法比安说着一串悦耳动人的奉承话,夹杂着潜在提议。说是谈生意,明眼人都知道实际上谈的是什么。就算不提密党的涉入,瓦萨里为了不引起明面上的不和,照旧暧昧着并不表态。他私下以为他们没戏。
不过该谈的照样得谈。副部约瑟夫在一旁冷眼听着,全然不配合的样子。他也就是在希拉不在场时才能做出这副模样。不过虽然林兹利在上议会大打官腔,军部目前在想什么,几乎人尽皆知。对他们那帮职业军官来说,大打官腔还不如大打出手(还一味认定二战假如不是下议院一帮软蛋照着普鲁斯特的面子先退一步,便肯定会打赢得更漂亮)。去哪儿打还是老地方,至于怎么打,怎么善后,照样熟悉得很。
他和真木都保持一种不受欢迎的意见:他们的问题不在哈斯堡想或者不想做什么,而是在于维图里是否决定直接插手。更微妙的,瓦萨里。
瓦萨里的瓦萨里行事和性格截然相反——他的手段是七成以上可以被预测的,基本离不开幻术师与幻相师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虽然在永恒之塔为评资历打得厉害,参考安东尼克收集整理出的近五十年魔党议会行政代表的实际投票趋势,虽然谈不上一致对外,两派综合外交政策上重合度不容忽视。说是斗争,不如说是种不健康的共生关系。他们的相处方式更类似于一对合约夫妻,因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联姻关系不得不通过各种的尝试耽搁着。
亲王名义上的死对头普鲁斯特近期沉迷于完善反驳“反人体炼金与实验”论文的最终稿上。照无尽晚报文化版副主编的话,他打算“极尽120页彻底性地毁灭这个不受欢迎的主流论点”。像蛋糕上的裱花,这个命题恰到好处地把希拉II,牵连着双塔的首席亡灵法师都骂进去了。您说所罗门期刊如何能给出120页的版面?只因为他是普鲁斯特。
瓦萨里家鄙视链清晰可见。灰袍视中洲封地为粪土;紫袍视灰袍意见为粪土;贵族视魔党封地“冻结”条例粪土不如。最容易出问题的一环,最终还需要回到大公一派上。月落城谁家的保守派都分享这方面的诉求,话是这么说,个别血族诉求格外迫切。他们谈得可是哈斯堡外围势力范围内最富饶的地区。没有之一。
有时候他希望有资本屏蔽掉这些嗡嗡作响的背景音。有时候他又希望自己能亲自介入,参与到尽可能多的族内布局中去。阿德莱德由衷感谢海德里希的失策,虽然换个位置他不一定不会同样如此行事。
他熟练算计好了政策,单单却忘了人情。不过话说回来,旁观议长为同一类型的重大失误反复买单,还是比较有趣味性。
他们都知道这在上议会制造了一个短暂的缺席机会,一把空椅子。虽然因为按照正常时间发展估计,提议还处在草案阶段,他必须现在或者从不做它。[1]
他们的立法人带着见习生为了尽量完善几个附属章程已经紧急接连不断地赶了四个月了,这还是在一名见习生“碰巧”在法院图书馆碰到梅策尔德关于公民财产法的,未署名的手稿之后。阿德莱德确切地明白——百分之九十五明白,没有什么是美丽的巧合。
他在法比安背完了几段的宣传论点之后,停顿了一下,显得比较赞同地点了点头。
法比安终于在上周工作日结束前终于和布鲁宁的文秘说上了悄悄话,为了这个他值得得到一个礼节性的吻。经过二十多年的反复碰壁,阿德莱德觉得他们最近顺利得反常,不过不到投票完毕,一切还说不定。在发言提案前的红月将他外派到中洲也算议长的最后表态,阿德莱德认为这不大委婉。
就算用最激进的估计,就算预案这么反复打磨,他心里也通透着呢:他们很悬。海德里希友情缺席,威廉姆还在呢,公爵不仅立场一如既往地明确,手里还拿着正在无尽城跑腿的高层喽啰克里斯蒂安的票,感谢老派的扈从制。
军部一帮鹰派和他们情报部长大概一样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中外办——还是别提中外办那帮随心情投票,表面事不关己,内在唯恐不乱的感性血族了。新党对提香和玛蒂尔达上议会投票规律的侧写? 估计还不如让赫尔曼蒙着眼拿墨水在科文部千疮百孔的墙上甩几笔更精准。
“确切地说,侯爵,这是我们现阶段能提供的最佳报价了。”他稍作遗憾地摆了摆手,在特蕾莎有重新夺回西里西亚区的意图下,奥方对他们货品的需求几乎不可掩饰,他们目前还不差中间受争议的这些差价。
至于他们亲爱的亲王?他反复试探,上周甚至借故登门造访,希拉每次都轻而易举地将这个话头一举击毙。
不过这一如既往。他们在赌希拉弃权表示不干预,甚至间接性支持。不同与密党长老会黑白分明的投票规则,帝国鹿里弃权这个选项,特别在附近这几十年,相当受欢迎。问题是亲王手上还拿着名存实亡的亲王配偶的两票,让本来就悬浮在半空的修正案的处境更加危险了。不管怎么说,他们下午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咔哒。仿佛能听到银币落地的声音。伏勒悄悄拽了一下他的衣角:克里希让步了。“那先就这样。”他微笑着站起身示意谈话结束,果不其然。
与随同人员离开时,他短暂地端详着悬挂的十二面金边镜子里相似而不同的映像,每一面都象征着不尽相同的可能性。
...Ιρις...
埃德加放学回到宿舍,也就是维图里新党的临时老巢,给自己倒了杯白兰地,一边小口啜着,一边考量着他与诺丁海姆小爵爷的关系。
他们认识的时间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实际上能腾出来相处的时间就更短了。以赛亚已经缺席四天了,在稍微好些的日子里他会撑着上课。
这意味着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他父亲当然意料之中地旁敲侧击,反复催促。但埃德加认为这类事务仓促不得。毕竟他们要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联姻,而以赛亚暗地里期待的也大概不是诸如此类的单纯公式化的关系。只不过,埃德加握住杯子叹了口气。
是的,他可以给他教科书式的浪漫,可以踏入骑士小说范本恋人的身份中。他放慢速度和男孩在琴房四手连弹,在监护人管家先生的视线中共进烛光晚餐,在室外树下阴影处共同读一本他自己绝对不会翻开的书,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种带有合约含义的关系中,正是如此。
可是他认为以赛亚所期待的那种被极尽理想化,浪漫化的关系,或许经不起长期维持。他可以玩弄权术,玩弄人心,但冒险将自己的也赔进去?在少数时刻,他甚至无法与他睁大的湖蓝色眼睛长久对视。
尽管如此,大部分时间还是无法事如人意。
地球仪形迷你酒桌上突然出现了一封递柬,他将水晶酒杯放下,从侧面拆开快速浏览,眉头皱得更深了。
埃德加从写字台上取下羽毛笔,在有契约效应的信纸下方空白处用标准的花体字写下了 “准。感谢您的邀请。静待阁下即刻宾临。”
他刚刚整理好一个中性的表情配合坐姿,临时最高祭司就出现在他面前,脸上挂着一个同样中立的,主要用于解脱人防备的微笑。
“突然造访,埃德加·海依·卡莱尔 gen. IV,打扰了。”
“不忙,”他注意到客人并没有提及他的爵位或是姓氏。他在这个关头接待阿佩普祭司不知算是什么。不过送上来的时遇有什么不欣然接受的理由。
“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么。”他起身,和祭司一同坐下,双手十指交触在膝间摆了个菱形。
“换个角度说,我或许能帮助您解决一些问题。”一世好整以暇地说,到迷你吧台前给自己倒了杯酒,空闲手做了个请自便的手势。
“哦? 愿君详述,” 虽然祭司这个(这些)人不到关节上决计不会将手里的牌亮出来,他只是乐衷于陈述这个事实而已。
“根据保守估计,我与您可以试图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一部分共识。”
“我希望您带来了好消息。”
“看您怎么说,不过,” 一世故意停顿了一下, “短时间内我不认为会出现更令人振奋的了。”
“当然,” 他皮笑肉不笑地点头表示同意, “这么说您定位到代理人的行踪了。”
“可不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他们突然对门厅的落地式衣钩表示由衷的兴趣。特别是避光一面明显小了一号的校服外套。噗噗,害他们拿着名单从A到M一个一个找了半天。
大多数都成了您的零食了。一世后发着责备了一下。
阿德莱德表情维持不变,握住高脚杯的手却攥得紧了些。 就算是不完全的猜想,这也会从根本上改变大多数的布置。他并不愿意看到事态顺延着这般的轨迹发展下去。“我相信您们一方已经反复核实过了,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诺丁海姆并没有相关记忆。”
怎么总有人反复考验他们的耐心。“也许。也许小爵爷并没有表露出相关记忆。” 他们学着这个新党家伙说了一遍。可惜现在还不能搞死这个虚伪的小白脸。一世感到老三对这个色彩鲜明的词组不悦地皱了皱眉。
保守地估计,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埃德加对于这个质疑一笑而过。
“这么说吧,” 一世知道想接近诺丁海姆,最快捷的方式大概是接触他的追求者。感觉到他此时被推动到了一个临界局位,他可能需要自己制造出这个机遇, “假设我同您在不久的将来, 和小爵爷发生一次偶遇……”
埃德加正快速琢磨着他能从中得到些什么,又如何将他的心理价位溢价上扬数倍,技巧性地报出来,他源于某种傲慢从未上锁的门突然被撞开。
以赛亚冲了进来,沾满鲜血淋的手不住颤抖。
“我觉得我可能杀死了什么人...” 他有些语无伦次,“或者很多人----到处都是,被剖开的......血,到处都是血,我不确定----”
他下意识地瞬移上前一把抱住了他,“----以赛亚,” 难说是路易斯还是卡特琳娜耐不住动手了。从上到下检查了一遍他的男孩身上都是皮外伤,埃德加才稍微松了口气,“你没事就好。”
“哦?” 客人眼中充满了看客的好奇,“那咱们就先不叨扰了。” 他们佯装遗憾地说, 几乎不可察觉地从头到脚仔细端详了一下他们的目标。他们未来的顶头上司就是这个毛孩子? 难道这不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么。这么说你希望我们未来的上司是个埃德加以上档次的家伙?不过你确定这不是个买一赠一、捆绑销售的买卖吗?我可没有否定过这种说法。
等到祭司用人类速度从容地走出大门,埃德加半托半扶着以赛亚在沙发椅上坐下,从躺椅上取来羊绒毛毯围在了男孩儿身上。从红桃木立柜里取出男孩儿的固定杯子给他倒了杯稀释一半的白兰地暖身,借机暗自深吸了口气算作给别人做心理咨询前,给自己的心理准备。
埃德加轻轻在他身前半蹲下与他直视,准确达到眉目之间和煦与担忧共存,“现在,发生什么事了?”
...Ιρις...
端详着科文部走廊玻璃窗显现的倒影,阿德莱德第二次整了整领花,他可无意成为提利安诺侯爵,机关算尽舌灿莲花,袖口忘记挽好的花边却成为了发言最深刻的记忆点。传闻已故的先知先生天文地理博闻广识,却经常忽略小计,平衡力还很差,曾给沉长无趣的议会制造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艾德,你没问题的。”赫尔曼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这种时刻他总忘记他们按理说该保持距离。他试图在自己心中寻找自己感情尚未腐朽发霉的地方,很遗憾无果。他记得他曾在赫尔曼的房间里与他一起阅读一些据说没有用的闲书,那些故事谈到了王子,王子的情人与可以吞下整架马车的龙。他总是喜欢选一些惊悚小说,在得到赫尔曼惊异的眼神之后帮他整理好衣服,叫他不要怕。事到如今,他和李之间只剩下的是一种能够胜过时间和战争的平淡情感:它的基础不再是爱,而是联结。
这个我知道。“承蒙你的鼓励。” 至于修正案有没有问题,他们都心知肚明。“为什么天使穿着希腊长袍?”他说了个俏皮话改善气氛。
“因为他是个理想主义的白痴。”他们几人异口同声地回答,这个圈内笑话从不过时。
他们逐一进场时,帝国鹿所谓的公共厕所墙正在缓缓向上卷起来,上午草案在下议会以统计上显著的优势通过后,密切关注的,兴致勃勃来看热闹的,稍微有头有脸点儿的血族这时候都已经得知了消息,使得今天室内聚集得格外嘈杂。
阿德莱德踏过议会大厅新换好的银绿交接的大理石地板。在经过后勤部对于反复清洗手造东方地毯上的血迹进行第七次罢工抗议后,内务部副部终于趁机滥用职权批准了。这种高反光的装置,衬着蓝月下旬挑空天顶打的人造侧逆光十分怪诞,格外突出了各位大人们苍白蜡像般的脸孔。
几位司法人士还在利用最后几分钟就“这项草案是否符合宪法”这个古早问题进行激烈争论,虽然几乎每位大人都事先考虑好,不约而同地准备履行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弃权。阿德莱德对大公礼貌而轻蔑的目光回以招牌微笑,虽然在这个语境下并非是“Sei gegrüßt (您好啊)”、“Guten Tag (多美妙的下午)”之流,而特指“Schleich dich (一边儿玩儿去)。”
“……我深刻地学到了,世界上再没有比英国更美丽,更奇妙,更动人的风景了,” 隔断拆完的当儿,刚刚从维图里驻不列颠使馆出差回来的约德尔正在和上司侃侃而谈, “假如您敢于说些什么真话和新的东西,他们就会感到惊奇,不知怎么回答才好。第二天日落,他们就会打发秘书血仆来投诉说, ‘您说了十分失礼的话。’”
“收获不坏,” 玛蒂尔达笑着说,“既然如此,深刻体验了的先生,您有没有猜到去英国是去干什么。”
“原谅我夫人——我的好太太——这是一个问题吗?我每周都去长老会大使道格拉斯家里报道,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礼貌的血族。”
“哦,是这样么。”
约德尔转口道,“艾希礼也十分义气地帮忙引荐了新党党魁。” 那个如沐晨风,背后插刀的梅苏塞拉名不虚传。不过经他观察,谈吐之间说是新党,实际行事和他们家温和保守派贵族没什么本质区别。
“我怎么不知道你和斯金勒熟识到了直呼其名的关系。” 一点即明,小子还是有点潜质。
“说实话,我在随行中的地位太低,本来没资格介绍。不过同行中累积的人情嘛。” 中洲是个很小的地方,月落城更不大,艾希礼竟是他转变前工作单位的驻英报社的同事。
“收获颇丰嘛。”玛蒂尔达坐直了微微向前倾身,恢复了愉快的神色。居然让他混到了维图里新党的茶会,她调侃地套用了对付摄政长老的刻薄话, “假如我有的话,这时候应该邀请你借用私人牧场。”
阿德莱德抿了口有色无味的会议饮料,顺便隐秘地瞄了一眼怀表。
“秩序,秩序。”莱茵哈德拉长着尾音,拿文件纸卷敲了敲桌子。上议院议长不愿主持这个所谓史无前例的投票活动罢工了,只能由他顶上。对于这种程度的合法叛乱,他真的有些审美疲劳了。
蓝月三点关门前最后两分半钟,他们家亲王才不紧不慢地拖沓着黑长袍走进来。——身边跟着脸色格外苍白的桑德兰主教?
“看够了就再搬把椅子来。”希拉懒洋洋地说,议会实习生才回过神时它已经将右手议长的空椅子征用到了左手边, 等桑德兰坐下后才徐徐就坐。
所有视线都集中在了左翼那把椅子上,没有血族说什么。
片刻后,议会大厅又恢复了嘈杂。
“我们对教廷有关人员的怀疑,” 在他身边,威廉姆特意顿了一下低声说,“是毫无底线的。”
“再不來根烟我就要死了。” 阿德莱德轻轻咳了一声说,有时候,一根烟真的只是一根烟而已。[2]
“原谅我,您本来就死了。”公爵照旧谈笑风生,“听说您今天或许要创造历史。”或者说不过是将注定会通过的章程提前了几年。
“祝我好运吧。”他摊了摊手表示无可奈何,向演讲台走去,没有什么能影响他的好心情了。
“现在,议员代表们(他抬起右手致礼,这是一个被科文部赞助学者研讨了许久的姿势)。我们本来准备了超过五个小时的讲稿,” 阿德莱德笑了笑,“不过还是长话短说了罢。” 他相信们都已经审视过提案条款了,或许还是许多遍。然而,这并不是个过场。
“每位血族都有拥有一个财产:他自身,除了他自己没有血族有这个权利。我们可以说,他的手与脑的劳动完全是属于他的。[3]“
他用余光扫了一眼上议院三排,帝国鹿宣讲时即时投票规则玩儿得就是心跳,这时立场明确者席前的红色,绿色晶石已经亮起来了。前排 6:6赞同反对,他们目前还情况还算不错。
“每位自然人,于情于理应当拥有个人资产不被占有的权利。他拥有个人资产,否则他无法拥有个人独立性,无法作为积极公民拥有社会话语权;因此他人无法在不侵犯血族与血族之间最基础的公平与正义原则的情况下去剥夺他人资产。[4] 除非这个, ‘我的’和 ‘您的’的分界无法存在。” 为了避免不必要地冒犯到中间派法院官员的神经,他在最后时刻把演讲稿上的“自然而然”改掉了。在权利人利益的合理性方面,还是从劳动理论来论证比较稳妥。
“每个勒托里亚法人都有和平享有其财产的权利。在月落城,除开为公共权益并受勒托里亚基本法和斯克伊瑞斯条约一般原则所规定的条件约束外,任何血族不得剥夺积极公民的财产。[5]“
第一排席间最后一盏蓝灯亮了,希拉果然还是弃权了,伙同着伯爵那一排的布鲁宁和乌里诺夫。
他缓了口气,“我们所说的财产,不仅仅限于有形资产,更是公民的经济利益,与具有经济价值的合约。” Lex Laetoria基本上在财产所有权方面照搬了Lex Solomon. 由于对于魔界频繁征战转手的领区考虑,所罗门对于固定资产所有权问题的处理,委婉地说是非常灰色的。”
大厅忽然变得非常安静。他看见后排提香特地起身瞬移到克里斯蒂安椅子前,帮威廉姆大公按下了他缺席血仆的否定票。那家伙之后才撇了撇嘴,忽悠忽悠走回到自己席间翘起小指按了弃权。
“这项基线公民权利,二战之前就应该被承认了。我们目前可以做的,是在月落城氏族封地里承认,没有血族有权凌驾于我的权利和自由之上,而我也不能凌驾与其他血族之上。” [6]
说了这么多,他们现阶段的目标仅仅是修正基本法承认公民财产权,关于血仆契约,中洲封地所有权,议会争议领土征用权等等政策雷区都暂时策略性地避过。毕竟正式认可是第一步。
上议院12:9,16票弃权, 在桑德兰到场,玛蒂尔达投了赞成的情况下,他们创造成功了。
“谢谢。”他微微低头,感觉天顶的环形光倾照在指挥台周遭,他抬起头,一边微笑着迎接台下接连不断的掌声。
...Ιρις...
以赛亚蜷在长椅上,手将双膝拥得更紧了些。
“我以为我在一间暗房里醒来,周围是一片不可分辨的噪音,”他咽了一口白兰地,继续回忆道,“还有一种鬼绿色,类似萤火虫的东西。”
埃德加有些担忧地注视着他,不管是炼金术师的强酸,巫师被腐蚀的光元素,还是星沙,这永远不是个好征兆。
“我身边有一名戴古怪鸟面具的黑袍人在谆谆教诲,絮絮地让我将长桌上的什么顺着肌理切断,从两边剖开。”
“我相信你并没有这么做。”他鼓励男孩儿继续说。
“嗯,”以赛亚点了点头,“我反复拒绝了,最后他不耐烦地抓住我的手,顺延着什么冷而湿的东西切了下去。”
“我将匕首扔到了地上,他快速说了几句听起来像是训诫警告的话,便推门离开了。”
等他稍微冷静了些继续说,“等油灯重新亮起,我才发现。我身前是一具尸体。”
“噢,以赛亚。”埃德加凑上去将他眉间的褶皱吻开, 他没有应和,也并没有避开,“这不怪你。”
“假如仅仅是如此就好了。”他们分开后,以赛亚有些倦怠地合上眼睛,摊开暗红色的双手,“我在府邸附近再次醒来,遇见的是林区中一排尸体。”
“听我说,我们会一起解决这个的。” 埃德加轻轻握住了他的手,有些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时间撞得太巧了。
[1]Empty chair crisis,勒托里亚上议会与会期间缺席按照弃权处理。
[2] 借代了据说是弗洛伊德对于雪茄的言论。
[3] 约翰·洛克的财产权劳动理论, John Locke, Two Treaties on Government (London: Printed for Thomas Tegg et al, 1823), 116.
[4] 克伦威尔和伊尔顿对于此类的财产所有权与社会话语权,投票权做出了议题关联。Daniel W. Rossides, Social Theory: Its Origins,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 (Rowman & Littlefield, 1998), 54.
[5] 关于财产权的定义问题参考了欧洲人权法院的解释,A1P1. 欧盟的定义比起联合国等等的更加具有弹性。Gudmundur Alfredsson and Asbjorn Eide,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 common standard of achievement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9), 367.
[6] Micheline Ishay,The History of Human Rights: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Globalized Er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