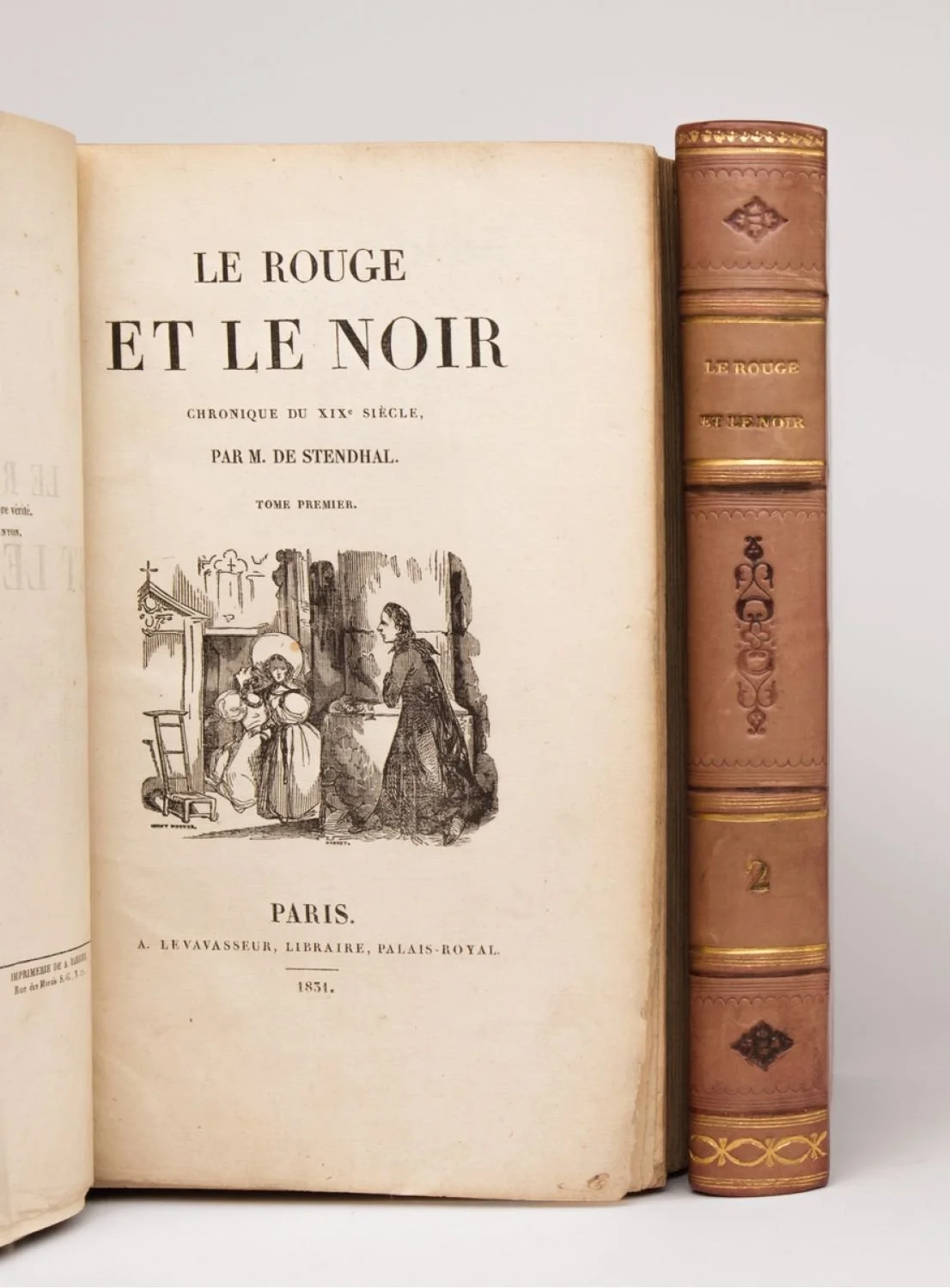Scorpiris Schemata 蝎鹫尾图式 第十八章:十二只羽翼
第十八章
Twelve Wings 十二只羽翼
主要坐标: 玛丽安太太的客栈,利奥波德区,维也纳,中洲奥地利, 1753. Frau Marjam’s Tavern, Leopoldstadt, Vienna, Austria, 1753.
深红庄园, 月落城东部,1752. Crimson Hill, Eastside of the Moonlit City, 1752.
建议配乐: 第一幕: Saman (Instrumental, piano), by Ólafur Arnalds.
第二幕:Bach, Violin Concerto in A Minor, No.1 BWV 1041: Andante, by Heifetz.
第三幕: Leicester, by Lambert.
...Ιρις...
房间虽小,却五脏俱全。大概没有什么比每天清晨拉开窗帘还可以看见那种温暖的蓝粉相间的清晨,与绿盈盈的皇家草场更让他满足的了。一只麻雀停在了他狭窄的铁花窗台正中间,欢快地啾啾唱个不停。
在冯·厄尔拉克和冯·海德布兰克诸君的规划下,维也纳突然变得巴洛克了。[1] 加百列一颗一颗料理好衬衫上的和小马甲的搭扣,打开天窗通风,可以听到室外的麻雀嬉戏声,建筑工地叮叮当当的敲打声。连利奥波德区也不例外,现在人人都要拥有最时兴的屋顶和最出挑的私人花园。
“加布,咱们搞定了,” 盯着众小工准备完了旅费附带的大锅早餐,玛丽安大娘用围裙擦了擦手,敲门探头到他房间里说, “完事儿了记得把锅碗瓢盆收拾到橱柜第三格里。”
“啊,好的。” 加百列用一片雪白羽毛当做书签,将诗集合上,抹平了封面夹角的狗耳朵说。 “谢谢您。”
他踢踏着毛茸茸的拖鞋到花园中采了几朵玫瑰,用鸽子蓝罩衣当做围裙兜好,熟门熟路地绕到旅店一层的后厨。
他本是想做理查德森哥哥最喜欢的改良版Ratafia杏仁蛋清蛋糕的,小手却不自主地伸到了白糖和玉米淀粉一格。
嗯。还是这些看起来简单的东西,最为珍贵。
他觉得不如将错就错,添入了刚刚好两人份的白色粉末。拍拍手召来一群好奇围观的水元素到小锅里。小火慢炖,正好在水沸腾前切开一只鲜柠檬,酌量将柠檬汁挤入迷你锅中。
“你也走失了么, 小家伙?” 加百列将碰巧吊挂在他耳边的家蛛接到手背上,小心地将它拢在双手之间,施法打开窗户将它放了出去。
他另外开起另一只小锅,召来清水,倒入奶油和玉米糖浆加热。弯腰取出木勺一圈一圈匀速搅拌起来,它们渐渐凝结,成为一种柔和的蛋白色。加百列专注地盯视着那闪烁着微光的一道道环形的涟漪。那只小家伙悬停在窗外,一动不动地好奇地用四只巧克力棕的眼珠注视着他。
你也走失了么……他也是这么对匍匐在树下阴影处的狮鹫兽说的。伊甸怎么会走进天界狮鹫呢。却是不带试探的,他只是想看看他的伤。
再一次正式遇见墨菲斯托,是这一纪的事了。他变了,却也没变。
除了他们这些守着伊甸这个美丽的荒原,任由时间在身周凝固的老家伙之外,谁又能保持不变呢。
或者可以说,这些年墨菲斯托尽力试图保持自己短暂陪伴在他身边时留下的印象。作为注重外表到偏执的程度的克洛西亚魔族,墨菲在他面前,连眼线都不化。他脸上有道很浅的疤痕,有意识地将底妆像面具一样一层一层厚涂,直至恶性循环,卸下妆时几乎面目全非。
呵,他在那时就是个圆滑世故的小魔兽。虽然略显年轻青涩,多少层伪装术、多么惟妙惟肖的天界狮鹫的壳子都藏不住他流动着算计精明的眼光。
现在也是老魔兽了。他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好孩子,却会将掉队的小天使完好无损地送回来;在一种扭曲的对公平的追求下,也没有去随手消灭他定义下比他弱得多的对象。
他曾忍不住去找过从第七天“叛变”到黄昏城,又从黄昏城到第七天访学的福斯塔斯博士问过他的近况,博士到现在想到那个满口荒唐的小骗子还是气哼哼地说不出什么好话,还能怎么样,还是老样子。
他活泼,好玩儿的坏孩子终于如愿以偿,可以优雅地独当一面了。这并不是说在潘城山腰上建有华丽别墅的成功,或是他隐而不报的欺诈神神格,而是可以不再依附他人的自由意志。
他特别喜欢去撸墨菲装扮的狮子鬃间柔软的绒毛,那是不带任何情色意味的,纯粹因为手感很好。想到这里,他嘴角不由微微上挑。在加百列的少数意见下,蜘蛛和天鹅出自同一位艺术家之手,为什么要偏袒其一呢。
恶魔狩猎灵魂以维生就应该被群起诛之么。难道并非只为了活下去?他当时因为这个,不知不觉和墨菲接连构造了多少隐形的隔阂啊。
算了,太多事都禁不起细想。他将两锅的糖霜淀粉兑好,还记得墨菲做给他的时候曾一本正经地说给两人的份儿是八比二,而不是四比一。
也正是因为这些日积月累的少数意见,以及他放掉被误判,被不公正的刑法处决的下级天使的玩忽职守,父神选择不将很多相关事务交付给他,他们达成了一种私下的默契和共识。
或是说,他其实理解父神有充分的理由在关键问题上不信任他。虽然天赋在水系群攻上,他一般被派在驻守而非攻城略地上。第二叶战役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他正在伊甸镇守。
他们当时都在逃避着什么。对于墨菲,是他被强迫着签署了灵魂契约的仇家与领主利未安森,他名义上的主人是那种主人。想到这里至今他仍然不由簇紧眉头,虽然墨菲微笑着什么也不说,他也不去问询他作为魔兽状态时依然存在的背后颈间交错的新伤旧伤。他后腰有一块无法再生毛发的皮肤,好像是企图被从背部将皮肤掀开未遂而产生的疤痕,他私下与拉斐尔哥哥交流过治疗方案,却被劝说将这不可能的活计按下。也是,用圣力为基的治愈术也只是雪上加霜。
对于他,哥哥和部下被米迦勒哥哥驱逐许久了,弟弟扎克尔被他曾经的副官沙利叶重伤,他还无法掩饰外露的低落……旧事还是不要重提。
加百列将几朵花掰碎了,连玫瑰水带花瓣倾倒进那粘稠的一团,又耐心地颤动中指和无名指施了一个克制的 “寒冰王座(Glacies-throni)” 将软糖冷却结块儿。他仿佛可以听到墨菲在他耳边轻声指导他完成这个小把戏的诀窍。这个坏家伙站在他背后贴得很近,手搭在他的手背上,引导着他们翻着特殊的手势,细长的指尖不着痕迹地滑过他手指的间隙。墨菲巧妙地利用了他们的身高差,好像只要他稍微不注意侧身,就可以将头搭在他肩上。
多么残酷而美丽的幻觉。
他不觉摇了摇头试图清空思维,抽出细柄菜刀,刀起刀落,将晶莹剔透的嫩粉色钝角方块切成规矩的一格一格。
他从木板上取出一块果子送入了口中,闭上眼睛,不着痕迹地用舌尖将沾在手指上的白霜舔舐干净。依旧是一样的味道,新鲜玫瑰花瓣的清香,到略带苦涩的回味。
他还记得。
他们都喜欢做这种费时的、看似并无用处的事。毕竟,再高超的元素法术幻化而成的只是糕点甜腻的幻觉啊。
真的是这样么,还是他们纷纷选择暂时脱离了既定的轨道。出于某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冲动。他们使岔路重合,又使双方不可避免地相遇在岔路上,合而为一。
漫天星光下,墨菲给他指出了人马座。星星有什么深意,只是后天的附加值。苹果很甜么,他从那棵著名的树上摘下来,这种最初凝结而成的甜香,轻而缓地掰开,像个虔诚的信徒一样真诚地膜拜,像个真正的美食家那样,饕餮着细细品尝起来。为了实现一种唯有切身体会的弥蒙的清醒,清晰和透明。银币两面的共振。还需要什么呢?柔光和晶石,溪水和磷火:这里和现在。
他佯装不懂状,额心相抵,合上两者之间的距离。意在互相欣赏和取悦。他漂浮在天空中,延绵不断的,湛蓝的天幕,他如此想。
呵,那时他们都觉得可以将星星摘下来,尽数收拢到体内,他的心那么不切实际地大。多么奇怪,陌生的感情就像命运一般不期而至。他们平躺在蔚蓝天幕下,树木葱郁的夏日剧场中,周身弥漫着清甜的草木气息,嬉戏般律动翻滚。
在一段时间内,这足够了。
他从抽屉中抽出一张蛋糕盘,将剩下的玫瑰花瓣混合着霜白糖粉洒下去,倾斜着案板用刀面将果子尽数平移入托盘中。
直到他发现他们将拥有一个孩子。这是多么意料之外,又预料之中的事啊。无论当时风言暗地传成了什么样子,他确信这是一个美好的意外。
他提示自己不要去想梅森。在那件事之后,他已经无法承担引起父神进一步的不满了。确切地说,虽然墨菲不会表示出来,他们都十分感激约书亚的默许——是的,作为约书亚个人,而非作为天主。
在战时与克洛西亚的王子私交,被原谅了。
将三分之一灵魂喂给先天孱弱的梅森续命,被容忍了。
他愿意承担全部的责任和后果,先一步用冰刀在约书亚眼前割断了六翼,耽搁了一段也被复原了。
然而父神的让步总是有限度的,他无意去试探那看似模糊的底线。
在那场沉闷的告解完毕,他拖着身子去将墨菲给他的素描画像,数世纪的信按照时间顺序仔细整理好,退回到翡翠府。他明白这是他被预期做的,虽说……
贝尔,我说个的,随时叫停,嗯?墨菲笑了笑,双手捧住他的脸,眼中非常认真。
嗯。他凑上前去在他的爱人唇边印上一个贞洁的吻。回去吧,墨菲。路西法哥哥的执政党HDP与魔族贵族的保守反对派HRC在多数政策上针锋相对,需要第三方势力平衡甚至抗衡,而中间派团体才刚刚显出雏形。
去完成建立一些美丽的东西。
加百列深吸了一口气,转身微笑,“理查德森哥哥。”
“看起来你也准备好了。” 拉斐尔立在门边,同样回以一个弧度无可挑剔的微笑。 “不急,在此之前,还是要先回味一下加布的手艺。”
作者注: 想起了塔罗牌ATU VIII. Strength.
© J.K.Ogburn, The Lady and the Lion, 2015.
...Ιρις...
蓝月凌晨六点,桑德兰侧躺在樱桃木四柱床上睁开水雾弥蒙的眼,抬手轻轻将希拉环住他后腰的手臂移下来。他有意将生物钟调到了它的相反面,意在尽量避开他们的交集。只是希拉作息时间极不稳定,又在深红庄园同处一室,基本上出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状态。
他抿了抿稍微有些干裂的嘴唇,已经坚持四天未进食了,很好。这至少让他从心理层面上感觉稍微好些。
一边扶着床沿起身,一边系好丝绸外袍的衣带,他走到主人房自带的洗漱室,体贴的管家先生已经预先让仆人准备好了浴池的温水,甚至添了某种古老的香料和一小簇应季的矢车菊花瓣。他重新脱下外袍,对折,在椅背上搭好,顺着马赛克砖墙慢慢滑入水中,闭上眼睛。还好希拉为了再度改良回溯试剂的配方,对着正在蒸腾的气化水银连续看了一夜,所以现在是少数他不受侵扰的,属于自己的时间。
他蜷缩起来,双手拥住膝盖,一双睁开的眼睛在膝间的空隙没有一丝生气,绯红瞳孔发散开成多芒星状,就像被随手丢弃的玩具玻璃球。
他直起上身,低下头对着水中的倒影练习了一个外交式的微笑,看起来像是某个Adel贵族为了完成画像抿出的不自然的弧度。他刻意吸了口气,闻到矢车菊那种深蓝、淡漠、即将枯萎的味道。
不愿再继续灾难化下去,桑德兰逐一伸出像骨架般的腿迈出浅浴池,从玻璃架上取下浆得雪白的柔软毛巾擦过依附在他皮肤上不愿滴落的一群水珠。
他凑到巨大的横幅古董镜子前收拾好了头发,不免注意到他的老朋友们:眼下挥之不去的暗青和嘴角下的两道木偶线。日积月累,他已经大概成了半个血族饥饿状态分类学专家。何必为这个感到困扰啊,桑德兰伸手抓了抓施 “恢复如初(sarcio)”烘干的亚麻色卷毛,不小心抓下了几束断发。他用双手撑住冰冷的大理石台面,低头轻轻地笑。
他走到步入式衣橱里自己换上了件宽松的,用成堆的蕾丝和荷叶边修饰的丝质长款衬衫,无意中扫过了内嵌的交织文字:K.CIEL FACCIO (凯特·希尔正在缝制)。路西法之吻的设计总监。[2] 看来希拉在他身上花了大价钱,为了某种源于美学,终于视觉的享受。桑德兰看着一排排卷好的冷暖白色及膝长筒袜,配套的镶嵌着贝壳浮雕的吊袜带,银制宝石或者琉璃鞋扣叹了口气,还是拉铃唤来场外援助。
“早安。” 他被指派的新任首席男仆悄无声息地瞬移到身边,比划了一个 “早上好啊”的手势,又抽出立柜中层可拆卸的抽屉呈到他眼前,请他挑选今天的配饰。虽然他认为这个举动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他还是指了指那套 “很衬他原本瞳色”的非金非银的葡萄藤雕花袖针和搭扣。
男仆将他双腕的锁链固定好,套上双排扣的浅金马裤,这个失败的设计有六个不同位置,需要单独扣好的纽扣,这还不算裤脚的八颗。他趁这功夫从一旁的高茶几上取了一颗无法消化的进口“草莓”素食软糖送入了嘴里充当代餐。日前上任仆人将位于腿后的排扣扣错了一颗,不巧被希拉眼尖地发现,于是就小题大做地需要重新招人了。
桑德兰选了一件色彩相同,款式相对简单的纯色马甲,双臂张开请他将下半部分的纽扣处理好,用疤痕累累的手整理好他颈前层层叠叠的的装饰性领子,取出亚麻饰带系好,又服侍着他在小凳上穿好高跟鞋上的方形搭扣。他别过视线,依然不大习惯被人伺候着穿衣——除开很小时候在侯爵府上的经历,少数需要他正装出席的教廷会议之外,他的衣着一直奉行着简化论。还好勒托里亚亲王不同于密党对种种仪式感毫无理性的追求,对目前中洲流行的长款羊毛假发充满鄙夷,连带他免了那份麻烦。
他短暂端详了一下穿衣镜中的映像,如果不看脸的话,更贴近洛可可糖果色的画中人,或是一个抽象的印象。
他不认识它。
他从玻璃立柜上取下希拉送的淡香水在脉搏处滴了几滴,橙花,白茶混合了摩洛哥薄荷叶的前调,目前来说并不能像据说的一样缓解心里的郁闷。清感官里新的淡淡花香与他目前的情绪相撞,转而又变成扰乱心绪的五月玫瑰,被金属气息玷污的香槟调,和来自东方,弄得让人发疯的琥珀。
这个貌似朴素的玻璃试剂瓶里装得是名为“耶路撒冷晨曦”的定制香氛,是希拉特意请叹息河边淡香咖啡的老板应和它的签名香“耶路撒冷之夜”调制而成的。虽然只是在希拉的庄园里打发时间,不过为什么不呢。
他挥手婉拒了杏色腮红和粉扑,“谢谢你,切斯特。”还是需要代表满意地点点头,礼貌地微笑。
希拉命人找了个不知世代的血族平民强行将他转化位了最低级的血奴,又在某种扭曲的理想的赏罚,诗意的正义下聘请了个瓦萨里幻术师永久性地缝上了他的嘴,将切斯特训练成首席男仆当圣诞礼物送给了他。深红庄园根本没有庆祝圣诞的传统。
虽然并不将责任归结于他,他根本不想和曾经的旧友有任何层面上的联系, “这里或是(送给) 奈瓦尔·格维茨诺维奇(当做试验品),” 希拉耸了耸肩随口说,根本没有留给他另外的选择。
“别客气。” 切斯特手上比划着,嘴角发力扯出一个怪诞的笑, 又表示“有事别忘了按铃,” 鞠了个躬退下了。
这就是他们目前的生活么?
...Ιρις...
他将浏览完毕的潘城视角(Pandemonium Perspective)和魔党口舌蝎鹫尾领域(Scorpitorisirium)放回了书桌上。太阳底下无新事,无外乎什么天界魔界就更新合约谈判拖延至今,什么金价波动性上涨,什么勒托里亚与欧克拉翰虚无派在但泽亲切会谈,什么费尔南德对卡玛利亚打击阿佩普恐怖主义行动表示支持,希拉甚至订阅了天界约则贝尔编辑的安格雷特刊在角落积灰,头版: 凯旋日米迦勒亲切慰问第一天驻军;圣子与会重申博爱宽容的天界价值观。
乏味。
书房墨绿底暗红色的墙围像是干涸的血迹,与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挑空头顶绘制的海蓝暗金星图壁画一起,令人眩晕的六面组成了一个长方体盒子,以一种几乎不可察觉的速度向他渐渐靠拢。
他有些不知所措了。在神学院,在罗马,甚至在梅斯他都有方法让自己忙起来做些什么。
然而,如今那些填充时间的办法统统都失去了应有的效果。他忽然感到一种时间几乎凝固的空虚,沿着木梯瞬移到快要接触到挑空天花板的顶层角落,顺门熟路地将La Divina Comedia第二卷取下来复读。这本纸张泛黄发脆的长诗似乎是样板书,他刚想从抽屉里翻找出来防护手套,却转念想起来现在他不再需要了。Blessed be, 颂赞血族与灰尘绝缘的体质。为什么清晨起床就这么充满讽刺。
他扫过斯塔提乌斯与维吉尔在炼狱中的相遇,
"Or puoi la quantitate
comprender de l’amor ch’a te mi scalda,
quand’io dismento nostra vanitate,
trattando l’ombre come cosa salda".
(如今你知晓了我对你的爱意
在我灵魂深处燃烧
此刻遗忘了我们那缥缈的空洞
将阴影与实体等同。)[3]
目前他处于一种身份尴尬的状态,并非是传统意义上作为被血奴主人调遣的下属。房间闪烁微光,像是金丝雀或者金鱼。或者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桑德兰感觉到一阵寒意,契约一旦签订即不可召回。他可以跑到中洲的另一端,却依然会保持着必须回到希拉身边的执念。
消磨时间。对了,我现在还剩下什么?时间。
生活总要继续,就算对于不死者来说。他习惯了每周与赫尔曼连带着一帮新党编外的公知或者艺术家在最高法院图书馆,议事厅附近中产血族光顾的咖啡馆,或是月落城东南湖畔紫罗兰沙龙所有的船吸吸二手水烟,谈谈纯理论或是艺术史之流的话题杀死时间。
每天傍晚或是清晨在山庄附近的林间散一小会儿步,思考一些抽象得无关紧要的问题,或者放弃思考任何什么。这让他短暂地获得了一种得到解脱的错觉,一种充满着隐含的悒郁,或是自我厌恶的快意。
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外放地厌倦这个世界了。最近他经常有这样的念头:假如无法和世界强行指派给他的位置和解,那么像他这样的异类只能用剩余的理论上永恒的时间作践自己。
呵,良辰美景,他一杯一杯,恨不得用浓得发苦的锡兰像香多尼一样淹死自己。诚然天天如此,延绵不断的茫然若失,平静的焦虑,无缘无故的恐慌,似是而非的麻木。固守着他发现自己从未曾真正相信的什么,确信自己失去了什么,却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时间失去了意义,他已经不再习惯性呼吸了。
他取出怀表看了一下时间,起身将但丁的炼狱篇放回原位,穿过二层藏书室外昏暗的走廊,没有点灯,他依然感到一张张框好的现实主义画像人物仿佛在观察和监视着他的动向。特别是楼梯转角的那筑斯芬克斯雕像,身上每一根羽毛清晰可见。它被蘸血的铁制荆棘环环缠绕,永远地停留在垂死挣扎的动态,人的面孔嘴张到最大,好像在发出无声的尖叫,双眼被两个血洞取代,眼下流着两道血泪。
他每次经过的时候都有些毛骨悚然的不安,无法欣赏这种赤裸裸的死亡美学。上一次与拉图卡同行时被副官留意到,不久狮身人面像眼前就恶作剧般被缠上了一道粉红的丝绒布条,貌似是从起居室窗帘上撕下来的。费安尼洛路过时觉得也挺有趣,便纵容着他伴侣的胡闹了。
一楼走廊也是少数庄园里有采光直射的区域,墙面上没有挂画,却阶梯式地挂着一层层希拉的绿植草药,在温室装置的监控下,在特质的盆栽中蔟蔟地愉快生长着。没有人会去动一位炼金术师的原材料。
好容易走到一层宴会厅前,他双手用力拉开了通往舞池的金属门,还是被扑面而来的灰尘气味呛得连连咳嗽。由于主人性格孤僻加上名声在外,庄园原本的双层宴会厅被改装成了储藏室,乱糟糟得堆积着数世纪积累着懒得处理的旧物。
只要有心,意料之中预料之外的都可以找到,他绕过生锈的全套骑士盔甲,几堆未分类的珠宝银币晶石,胡乱蒙着防尘布的叫不出名字的专业仪器,装置的连接线,多种语言的闲书堆,化学原料罐,用了四分之三的墨水瓶,边缘闪着微光的青花瓷器,猫木乃伊……银制勺子? 桑德兰注意不去踩到随意靠在墙角的油画,魔法卷轴,中央摇摇欲坠的黑色水晶吊灯下危险的空地,终于勉强算是安稳地到了占据半面后墙的玻璃水箱前。
水箱被极致奢华,配有一套炼金装置从内到外过滤着水源,顺便维持恒温,种满了水草,活珊瑚,与用骨头搭成的洞穴建筑群。池子底部堆着一层蛋白和紫红色的不规则半透明石块,希拉将闲暇时做的贤者之石随手丢进了鱼缸当装饰物,好像Opus对希拉来说与灵魂升华,精神超验或是其他什么崇高的目的丝毫没有关系似的,久而久之他也习惯了。
他俯下身从水箱下储藏柜里取出一小把植物种子,仿佛嗅到了食物的气味,一头孤零零的比拉鱼从被锯开颅顶的头骨中游了出来。由于希拉一直没有给它取名字,只能暂且被称为“鱼“了。在贤者之石的不断的浸润下它有些变异了,鳃和鳍之间的鳞片在黑暗中闪闪发出暗金色的光。
他打开翻盖将种子撒下去,看着小家伙津津有味地咬合锯齿磨起牙来。希拉之前一直只用它受害者的遗体切成小块喂它,连宠物都养得杀气腾腾,却不知这是在虐待动物。
终于将种子嚼完了, “鱼”可怜兮兮地游到玻璃前看着他。
桑德兰弯下身和它对视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放弃了,用袖子花边盖住手拾起地上的那柄勺子,从被施了 “寒冰王座(Glacies-throni)”叠加回溯药水保鲜的密封罐里挑拣出一块肉丁喂给了它。它一口吞下,欢快地转了几圈,又游回窝里了。
时间晚了七分钟的老爷钟在墙角发出吱呀的哼鸣,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Tomorrow[4],明天,今天和过去将来的任何一天混淆成了一团。他感觉自己在一片可视度为零的黑暗里接连不断地掷着色子,殊不知六面全都是空白。
被废弃的舞厅另一头角落挂着一张被色彩浓烈的深红丝绒遮盖的画像[Office1] ,可以依稀看到画框左边角落的铂金鹫尾花纹。他无意去窥探庄园主人的隐私,就像他不会将这间充满视觉记忆的旧室里的任何东西移动位置一样。
他在鱼缸上面默念“清水如泉 (Tersus-sursum)”将银勺子清理干净,轻轻合上水箱盖,又将勺子放回原处。桑德兰扶着宴会椅背坐下,久久将视线停留在鱼缸的中层层叠叠的水的波纹。
希拉本该杀死他的。在它对他们的交流产生厌倦之后,或者任由他那天精神力耗尽在梅斯。它不可能没有接收到他言语间的暗示。
原本按照规划,血族可以送他相对平静地尘归尘,土归土。虽然有些利用规则的嫌疑,这始终在情理之中,并不算是字面意义上的协同自裁。
凡人的身体怎么能支撑反复使用圣光呢,使用长祷词和复杂圣力咒文的神职人员因为圣力超过自身负荷,一般以来都早早在三十四十左右灯尽油枯。桑德兰自己在神学院就很清晰地了解这一点。而冕下也出于此考虑破例准许了克里特在三十左右隐退。玩笑,不出重大纰漏,红衣主教是终身制的。
他算是亲眼看着他辅助系的导师身体渐渐衰败的,刚开始是肺,无法正常呼吸,像肺结核患者一样逐渐咳出血来;渐渐扩展到肝和肾脏,出现明显的凝血异常,周期性休克;最后感官丧失,迎来多重器官衰竭。算是最后一课么,他想起来执事也是在三十中旬。
桑德兰自以为在前往神学院之初就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事实是在亲身经历时并不如此。他荒谬地高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
甚至对天界在中洲的士卒为何将漫长而痛苦的死亡作为先决条件而感到些许疑惑,殉难难道不该是自发的么。
他在桑德兰心目中其实早已经死了,在希拉违背他的意愿,将他们默认达成的共识置之不顾时。他们完了?或许吧。
不管具体过程如何,预期结果决计不是像现在这样僵持着。或许是为了惩罚他游离在灰色地带,他被强制永久性地驻留在了这个炼狱里----人造炼狱。
他听了听动静,差不多到了中午过渡到下午的时间,希拉大概终于起床,等心情不佳地磨磨蹭蹭,骂骂咧咧地终于清醒过来后套上件长袍,从传送阵出门猎杀人类去了。纯粹是经验之谈,在他未事先起来的少数情况,定会被抓回去赖上半个钟头的床。作为一氏族的亲王,在没有重大安排的日子里可以任意几点起床,也侧面证明了它的安排得当,何尝不是一种本事。
另一方面,他深切地怀疑它这么执着于每天有时间时一定要狩猎,或许是因为遵循某种古老的传统,或许更是对于可以成为受害者的恐惧和绝望的直接制造者,它深深地享受其中。
“卡玛利亚资历够了相当随意,至于勒托里亚?选择猎物是个相当个人的事,不过总得来说,拜欧克拉翰理想派传来的毒瘤所赐,不杀幼崽,艺术家和学究,甜心,”回到一层作为起居室的大厅,希拉又一次将受害者丢垃圾一样扔在地上,“他们有比当食物更高的意义。”
桑德兰从靠窗的沙发上转头看了它一眼,并不做回应。他从茶几旁的矮柜中随手取出本书做出占用时间的信号,非常应景的《永不堕落宣言》。天使长米迦勒大概是找文职下属代笔,战略性地从诸多神学著作中拼接撰写的政治宣传稿。
狩猎这件令人激动的事与为了自卫杀戮截然不同,而Shadow Transcend——希拉做梦都希望与桑德兰有朝一日能一同享受这种别样亲密的互动。梦境预备现实。
只不过看起来这个现实在这一纪大概无法变现了。
他看着圆桌上又一次原封不动的红酒。吃,或者被吃。希拉无聊地想到,往酒杯里滴了两滴立柜里水晶瓶中的透明试剂,有效防止血液沉积分层。
将外袍脱了随意搭在椅背上,这还是桑德兰在才养成的习惯。壁炉上齿轮暴露在外的古董钟嘶哑地报了三下,费安尼洛准点将公文用滑轮酒架推了过来。随便吧。希拉对着管家点了点头让他一边儿忙他的去,抓起渡鸦羽毛笔蘸了蘸猩红墨水,唰唰开始快速浏览起来。
...Ιρις...
落地窗外隐约传来一阵悦耳而悠扬的竖琴声,耳边传来的情感也非常个人化,像是某种祈祷,仔细分辨又像是对话。
“桑德兰,找你的客人。” 希拉埋在例行公文里懒洋洋地说,刻意将 “客人”念得像是形容某种害虫一样,头也不抬, “要我说的话,别让他们进门。” 这帮家伙总是连请柬也不递就擅自闯入别人的封地,别人的生活,仿佛中洲月落城所有的地契都默认是他家的似的。
桑德兰点点头从它旁边经过,却被抓住手腕。他顺从地闭上眼,在它唇边形式化地浅浅吻了一下,嘴唇上破了口,一直渗着一点血。
切斯特瞬移过来,递上了外套给他穿戴好,转眼又消失了。他透过半透明的彩色玻璃望向树林和庄园花园之间的空地,好像感觉到来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的隐隐约约的召唤。
“这么急着走?”希拉环着他移动到窗前,宣示所有权一样加深了这个吻。好像觉得还不够,又咬开手腕按在了神父的嘴边,全然不给他拒绝的机会。希拉有些不满地打量着他依旧不认真吸食的幼崽,虚弱成这样怎么见人。
理查德森?他眨了眨眼,好像需要确定什么。忽然他耳边吹过一道晚风,在这道几乎不可察觉的微风中,夹杂着往日的声音,侯爵府花园千瓣玫瑰的窸窣声与古早文献发黄纸页的叹息。
不对,确切地说。记忆回笼,像一张复合联结的透明的网,短时间转动播放起来。
作为访问门客与他的假期连续数次看似巧合的相遇,不属于外在年龄的见解,对晦涩的神学课题轻而易举,对答如流的回应——看在天主的份儿上,理查德森根本就不是修神学的,怎会尖锐地指出三位一体的超理性化,或是圣餐变体论的模棱两可之处。Chirst, 他怎么能如此盲目——持续地如此盲目。桑德兰深切地感觉他在一个被多方精心布置的舞台上,被引导着说着早已经准备好的台词。
“桑德兰。”虽然与预期境况实在有些不同,依然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
“理查德森。”桑德兰依然用了他在中洲的化名。
提前做出了种种的猜测和预想作为心理准备,当真正再次见到桑德兰的时候,面目苍白,双眼猩红,拉斐尔感到了眼见着约斐尔重伤不治时产生的无力感。
虽然与米迦勒对战时为了避嫌不会明显地刻意相让,路西法将高级诅咒咒文预留给了卡梅尔。Vocantem-larvae, 幼虫觉醒与神圣传召的双系组合咒文。未堕天前两名天使长就处处针锋相对,勉强可以算是连带清算总账。
本来约斐尔没有必要为长官挡下的,他全然无法从理性角度理解他的动机。
从而在低头在他病榻前端详时也无法产生适当的同情。或许是某种病态的好奇心致使他对着卡梅尔副官左胸腔虫噬腐坏的疮口持续不断地施放着治愈术,寄生虫群已经分裂繁殖了数次,目前的治疗措施只是将他的痛苦暂时性地延长。
“拉斐尔天使长......请您告诉卡梅尔,我......我不后悔。” 他将一只枯槁的手轻轻搭在了略显鼓胀的趋势的小腹上,“如果还有可能的话......请把它还给他。”
“我理解。” 他将止痛剂换成了肌肉松弛剂,额外地帮他妥善处理了后续的遗留问题,约斐尔还算是部门的得力助手,而他一直都在处理众人的后续工作。
约斐尔大概也知道如此爱惜羽毛的天使长不会允许他将它生出来。可惜即使是这样表态,也或许是充满讽刺的机缘巧合,虫噬已经扩散到腹腔,它还是没有被保住。出于契约精神,拉斐尔将未成形的婴儿从天使蛋中分离出来,装入浸泡着防腐试剂的玻璃罩中妥善保存下来,托人送给了卡梅尔。
他不好想象天使长收到时的表情,不过想来应该比较具有娱乐性。
虽然卡梅尔给他几个部门下了很多绊子泄愤就是了。
自从经常被调过来作为副手的约斐尔自愿成为了第二次战争的主要伤亡,这个微妙的位置空缺已久。最高天明面上是不能设立情报收集处的,为了维持圣父名义上的全知全能。问题是,圣父并不会时刻警惕观察着中洲与其他界每分的风吹草动。
少数紧急情况下他们甚至需要非常不好看地,秘密地将二级任务外包出去。天界的信息来源于恶魔苟延残喘的无尽之地,不失为一个可悲的笑话。
他迫切需要寻摸一个新的助力,一个适合的人选,可以胜任的,懂得章程也懂得何时和如何绕过章程,宽容但果断,仁慈却下得去狠手。再加上对圣力天赋的要求,也难怪事到如今依然是空缺。
拉斐尔并不像某些保守派去在意潜在人选是否是出生于天界。根据他的经验,很多灰色的位置圣灵做得远远相较天使出色,从约翰,马修到弗朗西斯。他对用新人并没有什么抵触。
从第一次在宴会上初次见面他就发现,桑德兰让他想起......他少年时。彬彬有礼,非常安静地在人群中,审慎地旁观着,偶尔做出一两句富有洞察力的回答。
况且前信理会副枢机不仅仅在他的名单上。他只是运用职权占了先机去接触结识了人家而已。他大致算好了日子希望借中洲带薪视察的由头接神父作为圣灵任职,问题就出在了大致的约数上。
往血族的转变是连时间系法术都不可逆的,这让他也很无奈。毕竟这不是像将恶魔绑起来扔在上埃及就可以直截了当地处理的事,试探培养了这么久就这么交给了希拉。[5]
“被安排为原先的项目去远行了,需要暂时离开这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拉斐尔如此解释。耽搁了许久,需要回到天界继续处理暂时交给安德略的公务,有很多决定他不在还是不方便。
“我明白了。” 然后呢?他唇边带着微笑表示理解,同时略微上挑的语调传达了一丝隐约的疑问。假如没有被转变的话,现在算下来已经到了日子了。
你认为走过圣彼得的门就结束了么?
桑德兰大致可以猜测到天使长原先的意图。错失时机。只是既然已经这样了,何必要正式表明身份呢?
并非是有什么东西破裂了。远没有那么戏剧化。他感到了某种对被剥夺了不可替代的东西的安静的缅怀。
他们在溪水边席地而坐,两人雪白的外袍完全沾染不上泥土和灰尘。
“很高兴终于把名字和人对上了,桑德兰,”同行的吉利安偏过头,从松松束在脑后的发辫中摘下一片雪白的羽毛[Office2] ,“权当是正式的见面礼。”
桑德兰道谢,用双手接过将它收到了外套的内袋里。虽然他还并没有意识到这枚羽毛所代表的含义,他的直觉提醒他这是一个重要的表示。
吉利安笑了笑,转而低头和灌木丛中的小草叶细细说着悄悄话,那朵小草微微颤动,害羞地蜷起了叶子。
“在少年时,我会在封地河畔像扑蝴蝶一样捕捉光源…揽在指尖感受它们的颤动。我会将圣光送到林间有枯萎征兆的野花杂草中,” 桑德兰有些疲惫地笑着回忆,“看它们重新绽放,再摘下来涉到水中,目送它们顺着河水冲走。”
“当我走入到一些黑暗的地方,”他顿了顿继续说,“有时候感觉会随之吸收一些。我将它带走。然后我会回到圣堂中,找个弗朗西斯或者多米尼克的兄弟(brother)忏悔......” 斋戒和祈祷,反复沐浴抹擦直到皮肤发红...他的眼睛亮起来一些,又暗了下去。
噢,桑德兰。理查德森想说什麽,最后只是稍稍前倾, 将手搭在了前教士的肩头。距离非常近,几乎可以嗅到玫瑰,鹫尾和血液混合起的冰冷的香气。
吉利安端详着远方的杉树和天空,似乎突然对那些充满了兴趣。他似乎身体不大好,掩饰住一阵咳嗽,脸颊上泛起两片不健康的红晕。
桑德兰抬起手,凝神,指尖点亮非金非银的光源。摆弄花草的吉利安忽然转过头好奇地“咦?”了一声,理查德森端详着他召唤出的圣光,推了推眼镜,眼中闪过一丝疑虑。即使是勒托里亚相对来说无属性的“清零”天赋,血族作为黑暗生物理应与生俱来地与光系互相冲突。
“这并不一定要被局限在过去,” 理查德森偏了偏头最后说。他需要仔细去研究一下相关文献——如果类似先例情况真实存在的话。
是这样么。
理查德森并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再次将手轻轻搭在了他肩上,亦远亦近的距离。坚强一点儿,你的时机还未来到。
假如真是这样就好了。桑德兰回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笑,不自主地微微凑向他的触碰。
亲近你的朋友,句号。潜藏着各种有趣的理解方式。[6] 莫非天界有意和月落城搭上线?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大概只能采取这种非常规的方式。根据他对理查德森的有限了解,他不会去做无法带来长远利益的无用功。可是为什么选择和勒托里亚?耳濡目染下他还是清楚这个家族明显倾向于天界永恒的敌人,路西法手下的堕天使党派HDP。
另一方面,说他对勒托里亚亲王的影响是有限的,大概都是言过其实。所以对于这种表态,目前他只能保持一种友好的观望态度。
远处传来砰砰两声哄鸟枪声明显暗示着送客,有时候希拉格外缺乏耐心。
“桑德兰……”
”嗯?” 他等着下半句,知道理查德森不管是在中洲还是上面都不会说无意的话。
”你知道,这不是你的错。我一直认为这是你最值得赞许的品质之一,然而考虑一下在原谅别人之前?”
我怎么可以, 桑德兰报以一个有些勉强的微笑。
理查德森也不再往前推,“Pax nobiscum (愿您内心得到安详。)” 他本来想说Dominus nobiscum (愿主与您同在)的,这种情况下想来也不妥。
“时常。” 但愿如此。
微光闪过,空地上只留下桑德兰一人。
以及一片铂金光泽的羽毛。
他继续让视线维持在上空,延长着那个回到了自己世界的错觉。桑德兰的红眼睛似乎在追着天空中的什么,浅浅划过一道阴影。
[1] 奥地利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著名建筑师,Johann Bernhard Fischer von Erlach和Johann Lukas von Hildebrandt。
[2]是个关于米开朗琪罗这个狂妄的天才的梗,这个家伙在别人注明出处的时候刻下了“米开朗琪罗正在制作”,现在进行时。向艺术史微妙的小细节致敬。
[3] Dante Alighieri, Purgatorio, Canto XXI, 133-136, translated to Chinese by Aran Latoria.
[4] 桑德兰化用了麦克白在得知夫人死了时的独白。
[5] Old Testment, Book of Tobit, 12:15, 拉斐尔化名Azarias在托比亚斯旅行时保护了他的安全。
[6]桑德兰想到的后半句是 “更加亲近你的敌人。” 出自马基维里。
[Office1]线索,桑瑞亚的画像。第二卷桑德兰会为了证实他的推测去揭开。
[Office2]加百列的信物,他自己的翅膀的羽毛。
可以用来做有针对性的“最后救赎”。
在第二纪末期与维图里的战争中有决定性的作用。

![[Epic Poetry] Song of a Grumpy Siren](https://images.squarespace-cdn.com/content/v1/5cf593045878000001fad3e8/1627867434422-F7IHJT8FKHAT202F6A6D/7966901874_76f23e852b_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