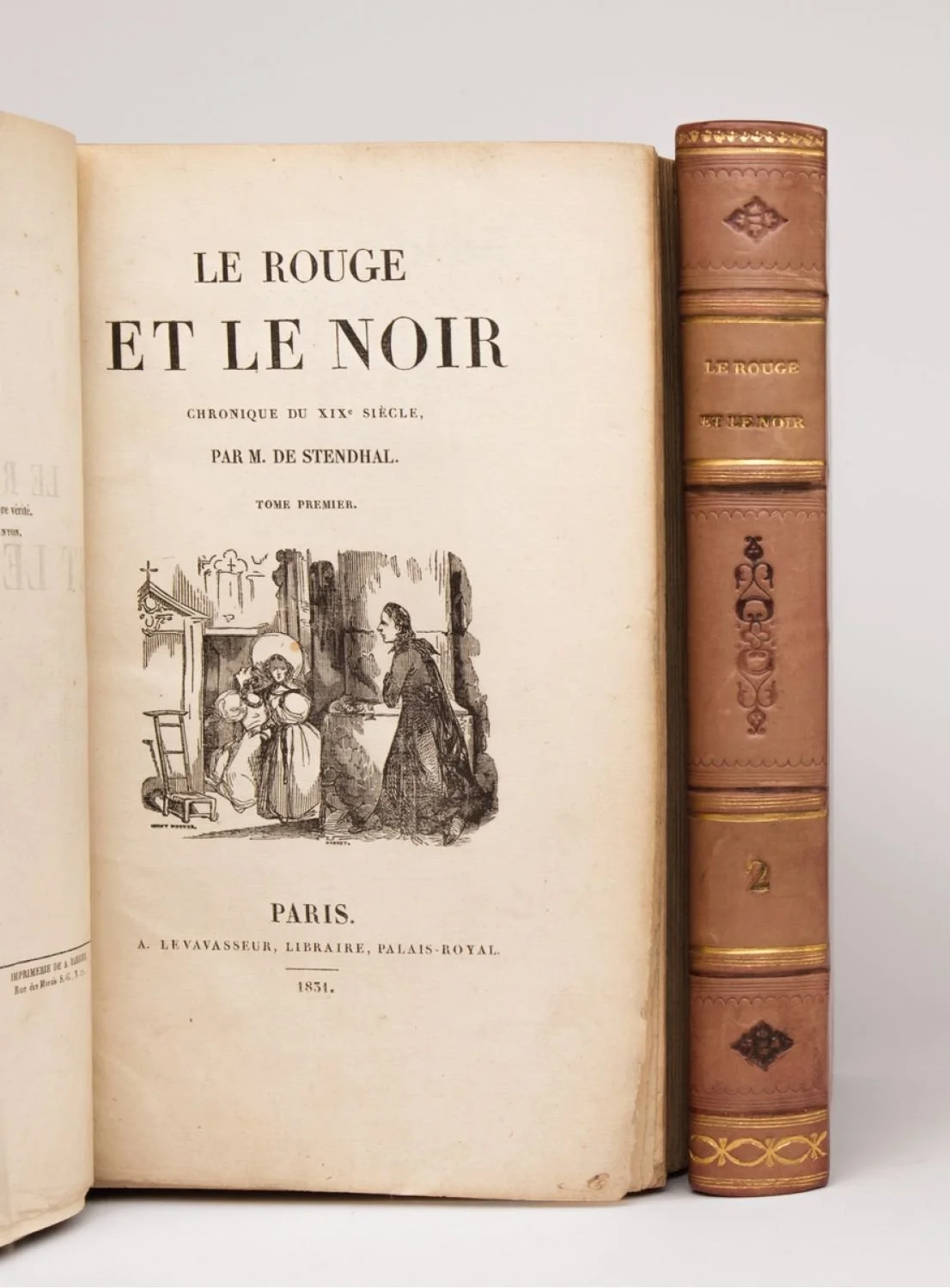Scorpiris Schemata 蝎鹫尾图式 第二十四章 月光和月光石
第二十四章
Moonlight, Moonstone 月光和月光石
主要坐标: 伦敦近郊,大英帝国,1753.
London, British Empire, 1753.
建议配乐: 第一幕 Arnold Schoenberg, Piano Fragment: No.2, by Yoko Hirota.
第二幕 “Alexandria” by Oskar Schuster.
第三幕 Franz Schubert, “Schwanengesang Ständchen”, by Paul Lewis and Mark Padmore.
第四幕 What is a Youth? By Aoi Teshima.
...Ιρις...
“Mama mia!” 那个一头鸡毛一样蓬松凌乱卷毛的睡衣女郎高声快速说,“%&)*#&%)(&)%#*(&(¥*%——@#&¥@#*(——**#&%*%——#*—&#@%*@%)*@&#&*)%@&@¥&*)&)&*@&\@#*(@#*…...(路易斯你办公室门口站着的两个小哥其中一个扑通一声被另外一个放倒之后到处都是血流了一地真是一团遭都渗到了地板砖缝里……)”
“&¥*Y)@()%.” 路易斯充满耐心地看着她胡乱从地上捡起丝绸外袍等等零件,将废物美人接连不断的噪音调成了背景音,起身到书桌前按了按铃。
“%*(%@¥&*%!%#…#&%*@…%(~%&)*@#)*%&@~*@4)!%(&(#@%*&%*@……%)@*.”
实话实说,中洲美人的保质期也就三五年。而既要保持新鲜,又要保持长情的诀窍大致就是,逢三差五再无缝衔接地换人,并且为了保证他名誉的完好无缺,花大价钱妥善安排好人家的后半辈子:要钱的送钱,要嫁人的送人。当然,这是理想情况,这次是有些仓促了。
“使命召唤,” 他换回英文说,不乏体贴地为她处理好套了半天没套进去的宽幅衣袖,顺手抓顺了他目前一任废柴美人的头发,“下次再见咯,甜心。” 吻了吻她额头道别。
“%@%*#!”
埃德加的血仆死在殖民地了。因为无心过失,而他则在某种程度上要为这种令人失望的机缘巧合,为他父亲无伤痛痒的小爱好的后续问题埋单。
我们的公子哥优雅地单膝跪下拿起雪白的抹布洗地板。路易斯·维图里 III的私人办公室,书桌,沙发,床摆在一处,不怎么含蓄地暗示着好像办公结束之后,就可以直接行使某种乏陈可谓的休闲娱乐。
他一边机械地分片儿擦着,一边无聊地自己和自己下棋,因为他缺乏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只好一丝不苟地照着棋谱行动,最后自然平局。
有些人滥用权力,并且对于滥用权力的权利享受其中。纵然话是这么说,他血仆的血仆并不是他的血仆,但这并不代表着温斯顿就什么都不是了。
好像这样的略施惩戒还不够似的,路易斯长老戴着他装饰性的金丝边玳瑁眼睛,悠闲地坐在一角的古早皮沙发上翻报纸:魔党党报。这种表面的雍容娴雅与他在看社会版的事实产生了喜剧化的对比。其实沙发也并非是真皮——过往的经验教训了他们血和别的什么溅在上面都很不好清洗。
好像这样还不够似的,他不耐烦地用皮鞋尖敲了敲埃德加刚擦好的地板,“上心儿,埃德加,可要上心点儿。”
“好的,父亲。” 他一口咬了回去,那是说,在脑海中。在现实中,埃德加默认,手上擦得更慢了些。
“你和那小子搞得怎么样了?” 鉴于“你把那小子搞得怎么样了?”与他目前的扮相不大相配,路易斯顺畅地改口敲打。
这句话让埃德加手上顿了顿,“以赛亚是个很认真的孩子。”
“哦?” 长老挑起眉,暗示性地拖长了尾音。
“认真得需要认真地循序渐进。” 事到如今他只得继续推托。他们必须在正式告白(其实他觉得是摊牌)之前确认祭司四世带来的消息是否属实,不然尘埃落定,反而给他人做了嫁衣,就非常不妥了。
“从道姓进入到了称名的程度了,真是好得紧。”路易斯当然继续过着嘴瘾。他这小子还是太年轻了。他扫了一眼第二版照着希拉的婊子明褒暗贬的长评,上议会又炸出来了个新党杂碎不知对他们来说是悲是喜,只道是预料之中。看看人家对家,不仅吃干抹净,合着已经到了同进同出的地步了。话说回来,找个审判所的不带回家放着,还登堂入室……还真是不乏生活情趣。
埃德加垂下头,试图用刘海掩住微微皱起的眉心。
“好了,别板着张脸。你真的以为这仅仅是对于你那走狗惹出来的小插曲的尾声么?” 路易斯点了根烟,拉长了尾音反问道。
他的动作立时凝固了。
“其实这才是。” 他父亲笑着说,“埃德加,她知道了。”
路易斯将夹着烟也不抽,饶有兴趣地目送着这臭小子抓起书桌上早就准备好的水晶瓶,顺便颔首充作告辞,瞬移消失在了门外。
...Ιρις...
礼堂的长餐桌上摆满了色泽丰富的菜肴,他将牛排用银餐刀切成一模一样的小方格,堆叠着摞在一边,什么也吃不下去。
以赛亚明白他所剩的时间不远了。
他自小就明白他身份所带来的种种义务,例如说,他并没有随心所欲选择伴侣的权利和权力。为了延续他们被诅咒的血液,他父亲,他父亲的父亲都几乎是草率地早早结婚生子,和时间进行着必败的赛跑。
不过,他或许可以在有限的选择中随心所愿,他钦慕埃德加学长。
不,埃德加。
埃德加是他一直以来想成为的样子,一个有见识、有担当的男人。既然他终究无法长大了,便随了这样的男人也罢了,这不尝是一种有所失有所得。
他从很早以前就知道他不能回头了。
在他的同学们纷纷都焦急地寻找“我是谁”之际,他分毫不想知道他是谁。这并非是为了逃避责任,反而是出于一种现在看起来已经将将过时的责任感。
“…...以赛亚,也欢迎你到我家玩儿哦。” 同学A顺便发出了礼节性的邀请,要想代代有钱,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决定了日积月累的金钱关系。这小家伙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拉关系当然要从小做起。
“你这个白痴,人家要去和学长过啊。” 同学B用一口礼节性的调侃顶了回去。出口胡说八道,也不看看人家是谁;也不看看你家是谁。B君转头堆出一脸笑,“倒是海德薇阿姨可是想你了,有空过来玩儿啊。”只要在家谱树上发掘出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关系,改明儿他不想来也得来。
“不了,谢谢。”他一口回绝,也不知是在回答谁。
当他的同窗们都激动地商讨着假期去谁家叨扰,去哪儿旅游时,以赛亚正在考虑是不是比起父亲和爷爷,他可能要提前死了。
从陷入细思恐极的幻觉,到更加频繁的心率不平和虚脱,种种症状无不都表明了好景不长的事实。他明白对于现实的冷嘲热讽,他只有接受的份儿,却又心有不甘。
在别的孩子都在去郊外和父辈打猎,牵着猎犬在花园里不管不顾地疯跑追孔雀时,他只能坐在府里隔着一层遮阳用的纱帘窗边看书,看天,或是努力什么也不看。他想弹琴作曲,却也深知这不能当饭吃,也不能长久。
哈,哪个正常的孩子会潜意识地想吃了自己的宠物呢?反复撒娇哀求之后,他管家叔父家教家庭医生组成的委员会才勉为其难地觅来一只纯种波斯猫,作为他八岁的生日礼物。
他在半梦半醒间吸干了他的北极星。管家先生只是沉默着随他一起将幼猫埋在了后院。
之后他没有再提过养宠物了。
埃德加学长。这次埃德加学长不一定能在他倒下的时候接住他了。在困境和僵局中他只能选一种,或者说,被动地被选择其一。任他四处逃避求索,依然只能走着早已被隐形书写好的路。
以赛亚当然没有准备好,可也没有时间准备了。
虽然说有人帮他准备好了:他周围总是围着莫名其妙来的转校生,给他的学习生活制造新奇和神秘感。
塔里克是少数他可以容忍与他同桌吃饭的人,在埃德加忙的时候他基本上就跟这个自来熟的新同学搭伙。或者说,他吃,塔里克看着,有时象征性地吃几口,一边诱导性地逗他说话。以赛亚只能喂他些他以为无关紧要的,心下许愿高中数学题和古典主义乐理果真算是无关紧要。
比如说现在。他们刚考完了试(他算是勉强做到了有始有终?),以赛亚一脸黑线地注视着他慢吞吞地将四分之一茶匙的土豆泥蘸着零星几点鱼子酱送入口中,满怀享受地含着,依依不舍地咽下,一丝不苟地用雪白餐巾蘸了蘸嘴角,表示吃完了。
“请问您是来自哪里的?” 他终于问。
“我是小四啊。” 祭司四世当然笑眯眯地说。
“抱歉,请问您是来自哪一方的?” 他转言说。
四世只是笑,还是没有反应。
以赛亚将银边叉子放下,短暂地停顿了几秒制造出一段人工的沉默,做出再次尝试,“请问您们是来自哪一方的?”
“哎呦。失礼了,” 他们眼里闪起愉悦的水光,有些甚至渗出了他们好容易从格维茨诺维奇家杂货铺淘来的物理性的屏障,这样看来更靠谱了,“说透了就不好玩儿了呀。”
“这样啊。” 他将埃德加的属下和维图里长老会的眼线从可疑人员名单中划掉了,看起来情况比他原先所想象的还要坏。确切地说,是更加繁杂。以赛亚决定当他因为缺乏关键信息想不明白,也就暂时不去想。
“很高兴重新认识您。咱们的小朋友,” 老二不死心地添油加醋了一句,被他在他们的思维宫殿里拿快速构思出现的板砖敲打了一下脑袋,“明儿得了闲不见不散呦。”
“嗯。” 虽然他们都知道假如事件正常发展,他们估计都得不了闲了。
...Ιρις...
当埃德加继续琢磨着如何与少年制造偶遇的时候——Cain Forbid,他作为少爷时的那些经历与花招都不可用——维图里新党伦敦的办公室的磨砂玻璃门被推开,“斯金勒,他们知道了。”
“他们,还是她?” 长老会与太后那一派启用的措施截然不同,是走程序和让程序走的不同。不过不管怎么说真是大大的不妙了。斯金勒翻开日程表快速浏览着试图抓出首席摄政长老的惯常足迹,另一只手敲着通讯器以备万一,叮咚。“太后现在在长老会——”
埃德加在腹中骂了几句,抓起呢子大衣往传送口瞬移,“现在就去让翠贝卡把那几只该死的鹅丢到泰晤士里去!”
埃德加马不停蹄地回到宿舍,他一整天都没有恢复他正常的姿态。他没看标签就从酒架上取出一只玻璃瓶,并且喝了很多,也不只是希望以此钝化还是激化他的情绪。然而血酒雪上加霜地赋予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和更加鲜明的性格)。
他多么希望能径直合衣躺在沙发上,一觉睡到天黑啊。然而他只能坐回书桌上,从抽屉里抓出一张事先喷了好容易从Cafe de Toilette候补名单批下来的畅销古龙水的信纸,指尖在笔架上游移了几秒,还是选了较为安全的深蓝色墨水笔,开始奋笔疾书起来。似乎有人经过时探向了窗户,不过不管他。
亲爱的以赛亚:
希望这封信安然无恙地送到你手上。
我很抱歉如果有些唐突了,不知是否有荣幸邀请你今天傍晚五点半在老地方一起欣赏夕阳?
他略微停顿 了一下,还是决定保持简单一点。
你的,
埃德加
“翠贝卡!” 他失礼地喊了一声,得到秘书小姐疲倦地“嗯?”了一声,倚在主卧门边。
看到她老板一脸严肃地夹起信封,翠贝卡立刻瞬移回屋套了件晨礼服,撇了撇嘴接过信封,开门出去了。
...Ιρις...
象征性地吃完了饭,四世顺手顺走了张崭新的餐巾以备待会儿擦手。失陪一下,他们要出去清理一下摄政长老派来的杂碎。他们的线人日常浑水摸鱼,在关键时刻还是比较顶用的。
世事难料。被打脸了吧?当事人本尊来了。
他们默默地看着身着不合身的圣瓦伦丁讲师制服的卡特琳娜·维图里IV,为了体现摄政长老遭受自家元老欺瞒的怒发冲冠,凯特连头发都没盘就来了。
“你要是识相就别挡道。” 维图里的太后怒气冲冲地说,虽然荣誉讲师贴服到“曲线毕露”的绸缎制服让她狠话的说服力低了一筹。出于种种战略原因她并没有穿塑腰,从而将标准性的沙漏体型打回了原本的搓衣板身材。并不是说他们对维图里女长老的身形有什么多余关注,然而作为同样平板身材,却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人群视线聚焦中的他们对此不乏心心相惜的感觉。其实是幸灾乐祸吧。
“如果咱家不识相呢?” 老二横着跨了一大步,正好把他们挪到了草坪上穿插的小径中间,笑眯眯地问。
“别忘了你现在站在谁的地盘上。” 长老放慢语速警告,哎呦看样子是随时准备启动降临了。二世兴奋地想,他最喜欢使星沙揪下别人高傲的小翅膀了。据说凯特的四小只还华丽丽的,超级惹人怜爱。难怪维图里视他们家为过街老鼠:还是携带鼠疫的过街老鼠。他忍不住提醒哥哥,这次他们为避免节外生枝,根本就没带星沙。
“噢?愿闻其详。” 理论上说,伦敦封地直属维图里亲王。这是说,卡帕多西亚执政时期分封的正牌亲王的最近亲属。就算第三纪位置空缺了数世纪,摄政长老代持得名不正言不顺,处境相当尴尬。
这一切尽在不言中的阴险议题显然让现任摄政长老怒火更盛了,他们继续礼貌地看着她内心挣扎的过程,最后还是端住了架子什么也没说。
别低头也别抬头,当心不管怎么着儿王冠会掉噢。
“很抱歉,您似乎来迟了。” 他欠了欠身让出了道,没意义再和不讲理的争执,更别说现在看来可能会演变到争斗了。这不是他们的战场。
“他们人呢?” 她一定要找个由头活剥了路易斯他儿子的皮。不,不是算旧账,而是新账旧账一起清算。真是好样的,找谁不好硬是攀上了诺丁海姆家八竿子打不着的草鸡亲戚。真是头痛加上了棘手,她也知道自己拜这下九流的手段所赐失了先机,到现在只得尽力止损。一旦诺丁海姆家小子成了诺丁海姆-维图里,不管是元老院还是她,明面上就什么也没法做了。
“您觉得我们会知道么?” 您觉得我们会告诉您么?二世继续学着他的语气逗她玩儿,他对此十分不以为然。嘿!我在为临时代理人的性福幸福争取时间。
卡特琳娜好像也终于发现了这个,所以“哼”了一声宣告自己的不满,转身反方向瞬移走了。
他们不紧不慢地将还是没用上的餐巾展开,铺到冷冰冰的草地上席地而坐,二世将他们的下巴抬了起来无聊看天。四世用余光瞄住终于收到讯息的以赛亚匆匆从礼堂里走了出来。
跑快点,小亲王。跑快点儿。在老二糟心地喊出声之前,他成功夺回了对他们身体的控制权。最好赶快长大别被英俊无耻的小白脸骗上几十年……哼哼几世纪。
问题解决。他们目送着以赛亚的小身形逐渐埋没在树林中,为了以防万一继续让二世在瞬移可及处静坐着。他回到他们意识深处,终于在属于他自己的安静书房里簌簌挥笔继续涂写起来。很遗憾,言灵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下面就是筹划处理真正问题的时间了。
他们开始为临时代理人精心筹备一个史诗般的未来。
...Ιρις...
一切都是那么完美。
一片华彩初上的颓败景象。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从落日与新月遥遥相盼,蓝彩粉紫色的缎带天幕,到镜面河畔上依偎的两只雪白天鹅。他对这个手笔表示了适当的感动。
正如战争如此浪漫,罗曼蒂克也搞得像打仗一样。同样见血——却更加温柔婉转。
可是以赛亚突然发现他们的故事就像梳理精巧的骑士小说一样,工整得无可挑剔。时间停止了,好像之前的每一天,都逐步微妙而势不可挡地向着这一天推进。可到了此时,他反而茫然若失起来。
“我们还需要什麽呢,除了丝绸和香蜜”, 埃德加小心翼翼地上前拥住以赛亚。他实在来不及打腹稿了,只得即兴发挥,“还有月光……”
和诺丁海姆一起度过的时间,好像重新活过一次,多么令人激动人心。
“闭上眼睛。” 以赛亚转过身弓下腰,低头双手靠拢挽起一捧河水,“现在,可以睁开了。”
他的男孩将月光送给了他,现在他们拥有所有的了。他切换语调,不乏腼腆地轻声说,“噢,以赛亚,其实我也有一个惊喜。”
他从外套口袋里取出了戒指,戒面是一只莹润剔透的月光石。
以赛亚踮起脚尖,闭眼用前额抵住他的额头,“埃德加,你让我该怎么办呢?”
“一切都大概会好起来的。” 或许是一时间的失神,他做了个不该做的承诺。
如果能一直活在一幅画里,多好。
以赛亚将手伸到月亮前,透着月光石看月光。于是他笑了,可是他想哭。
人类成长的速度不尽相同,有人活了半辈子还是像个孩子,有的孩子被世事督促得少年老成。他比他看起来稍微成熟得多,埃德加这么决定。他注视着他细瘦的手腕,那是属于孩童的手腕。男孩的头才到他的肩膀,埃德加不由陷入一种深深的悲观之中。他不会再长大了。不,远远不止这样,他是维图里的亲王。
“你知道的,其实我很喜欢你。” 或许是这样,或许是别的什么。他如此反复,也不知是在说服自己,还是向他证明。
“我知道。” 埃德加轻轻拥住少年,这是他目前仅可能做的。如果他做得到的话,他不希望将这种命运强加给任何人,何况是以赛亚。
“我了解的......” 你是刻意接近的。没有一刻不比此时,他深深希望他们同样是为了爱而结合的。他抓住他的袖口,就像溺水的人抓住虚无缥缈的浮木。
“我知道。” 他有些哀伤地拂过以赛亚额前的碎发,试图垂下头亲吻少年的额头,后者却凑上前去加深了这个吻。以赛亚将浅粉色的双唇张开,猫舌头稚嫩而热情地探入他的口腔。
虽然并不是单一纯粹的动因,自始至终,一切都乱了。
以赛亚率先将两人暂时分离开,伸手从外衣内袋里取出了他父亲的婚戒,他希望埃德加拥有他。
然后就是夜幕降临了,可以呼吸到的雾。
他们找到了彼此,以赛亚却觉得他以此失去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