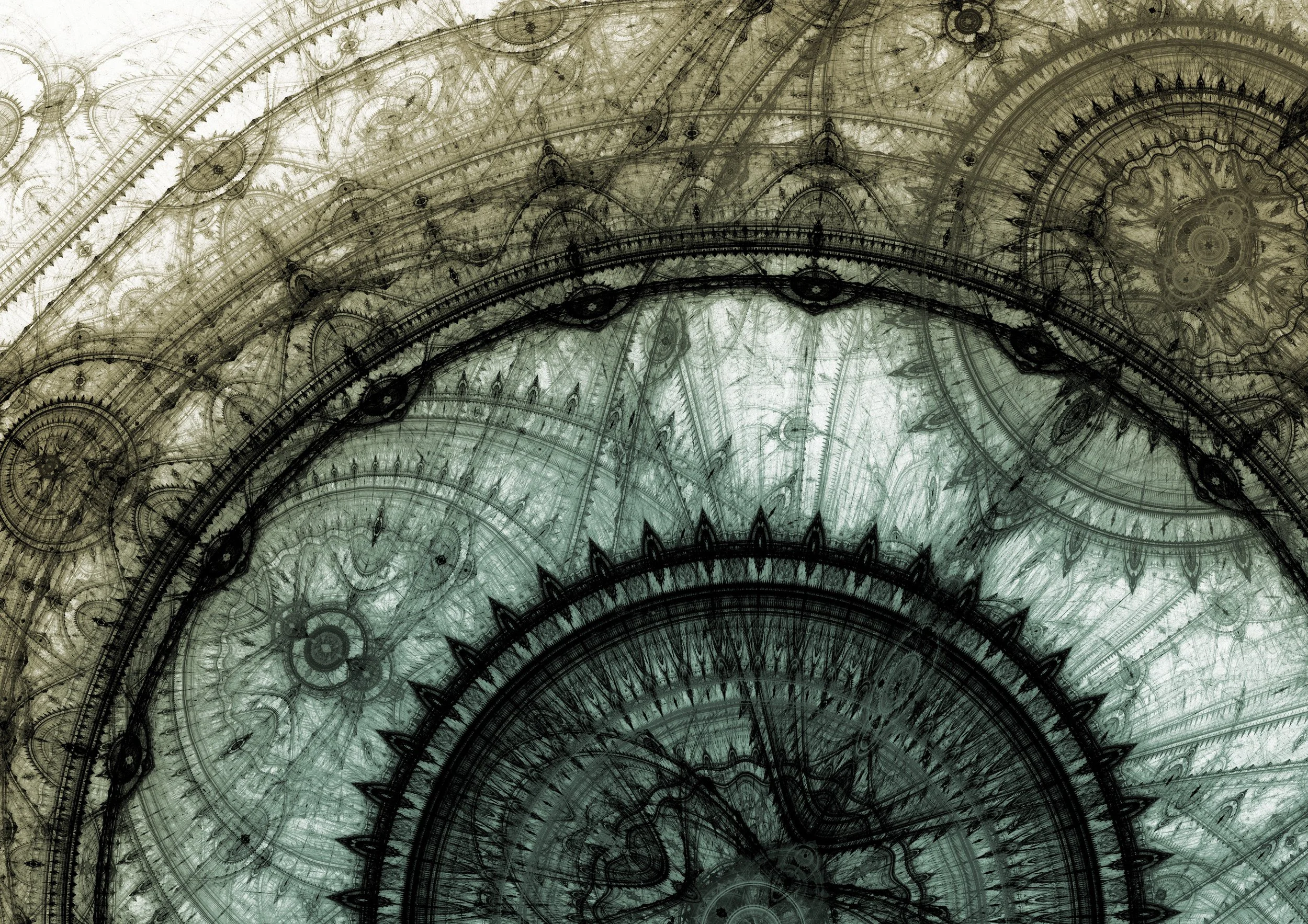Scorpiris Schemata 蝎鹫尾图式 第二十五章 主教的牢笼
第二十五章
Bishops’ Prison 主教的牢笼[1]
主要坐标 摄政长老城堡,维图里领地,月落城,1753.
Elder Regent’s Castle, Veturii Holdings, Moonlit City, 1753.
罗马,31 BC。Rome, 31 BC.
建议配乐: 第一幕 Valerie Broussard, “A Little Wicked”.
第二幕 Corde Oblique, “Le grandi anime”.
第三幕 Adrian Von Ziegler, “Queen of Thorns”.
...Ιρις...
卡特琳娜一边操着乔奈尔,一边想着她的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她穿戴好盛装华服,涂上张假脸,隆重入场时让满屋蓬荜生辉,用下巴瞧着一群沾沾自喜的看客,她就代表着卡玛利亚所有血族。是的,一帮屁民在给她鼓掌时根本上就是自恋地在给自己拍巴掌。
群众每时每刻的高期待,外加每时每刻对于她出丑露怯的高期待,迫使她每时每刻都处在警戒状态。就连这时,她腰上都箍着手工提花的蕾丝鱼骨束腰。
去他的吧。她终于将手伸到腰后,将那双蝴蝶结解开,任束腰狼狈地落到了床角一边儿玩去。
他们全然忘了二战时是谁在艾登·加西亚为求自保撤军时带着亲军顶上的,也全然忘了是谁刚下了西里西亚战场,为了让费尔南德一帮只知道投降的乌合之众苟延残息,就去和希拉决斗的。那可是希拉呀!使密党议会做挡箭牌,逼一个帽子还没戴稳的四代侍官去阻击二代亲王,他们也好意思。
到现在,乔奈尔手上说不定还留着她当时匆匆记下的遗嘱 (她把所有东西都留给梅丽莎她们几个副官了)。
她也不是不知道,她活下来了,或许是因为希拉任她活下来了。不随便杀女人和小孩?所以自然不杀女孩儿?直至今天,勒托里亚拆了十几招,冷笑着抖手收剑的模样依旧让她恶心。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她双手用力抓住乔奈尔的肩掐出了血痕,后腰使劲,动得更快了。她能半路带着密党和勒托里亚那帮疯子连同他们打不死的半兽人走狗打个平手,才不会折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上。
乔奈尔当然知道她心不在此,还是伸手捋过首席摄政长老额前铜红色的碎发,出语安慰道,“我们还有二百年时间,别过虑了。” 她或许能赢回来的。亲王在卡玛利亚法定的成年之前,至少名义上依然受长老院的教导。摄政长老是否继续执政,或者说摄政长老是何人,一切都还不是定数。
那是在长老院认同维持现状的情况下。鲜少见他这么甜言蜜语,她哼了一声,继续按住他,按着自己舒坦的节奏律动着。卡特琳顿了顿,低头直视着她最钟意的裙下之臣——不,她最长久的情人。
她当然需要承认,那件事做得并不漂亮。以至于出于某种不可调和的原因,他和她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种无名无分的关系。乔奈尔也不一定真的是把她也当成情人了,可能和他府上那几千张水粉画一样当做件新鲜物件。
可是她得到他了,这就足够了。在很长一段时间,每周日她都会穿着唯一的那身半新裙装,风雨无阻地准时到场,只为了去看他说话。当她终于得到他的时候是激动的,虽说人不能持续激动四百年,偶尔和乔奈尔在一起时,她还是不免会重新找回心悸的错觉。
她压低声音软语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对么?” 看在这些年的份儿上。
乔奈尔沿着床沿支起上身,将眼镜摘下来,在她脸颊上印下了一个浅浅的吻。
卡特琳有些不满地想,他脸色苍白,就像好几天没喝血一样。[MOU1] 她可以心不在焉,可他不能。
不过她确定他至少会好好投票。再加上她的阿格纳,任威尔士领主和刘易斯那个老不死的再怎么翻腾,估计也掀不出什么浪花来。
草率完事。她从他身上下来,随手裹了件搭在奥托曼上的衬衫,拉铃叫梅丽莎从牧场里取点儿存货来之后才瞬移到浴室,扎入早早备好的热水中。好像只要将脸藏在鲜活诱人的血水中,一切都会好起来似的。
...Ιρις...
桑德兰再次出现在同一个梦境的延续中。虽然他意不在此,也只好不以为意地做个局外人。
他有些倦了,对于这些似是而非、似曾相识的事情。过去和想象中的过去联结正一张错综复杂的网,将他缠绕住,直至窒息。
为了将过去,未来,和子乌虚有的过去未来拼接而成的画面屏蔽掉,他喝掉了希拉庄园酒窖里好几个月的库存。可这又有什么用呢?他们依然挑选着最不恰当的时刻重现,半真半伪,栩栩如生。
轻轻叹了口气,他在一棵无花果树下席地而坐,准备继续充当他自己生活的看客。那句谚语闪过他的思绪:守望无花果树的,必将享受果子;服侍好主人的,必将享受尊荣。[2] 真是好极了。
喷水池是城邦众所周知的汇点。不管是家庭奴仆要解决一日三餐,太太们要梳妆打扮,先生们要在血雨腥风的间隙休憩润唇,水源是生命线。
至于喷水池为什么被城建设计在了公用水井和洗衣店旁边,还是不去想它了。和他无关的,都被暂且定义为无关紧要。
他捧着一个陶器水壶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成功地做到了迤逦又局促。不过可以看出来,他明显不是常做这份工作的。
推断被证实,他将水罐像丢垃圾一样随手扔到了水井旁,磕了个角也不管,好容易挪窝到喷水池边,斜坐在了大理石池沿。
这时候罗马城人很少。旧的内战刚刚告一段落,新的内战就行色匆匆地来了。新结党的三人帮很快被经营成了只有两个人的“三人帮”,最后倒是成了“篡权的暴发户”和“投奔埃及的叛徒”。[3] 还在工作的人都行色匆匆,不过其实没什么好行色匆匆的,局势已经非常明朗,或者说,非常黯淡。
再者说,谁下午才被支使出门打水。一看就不是好人家的孩子,甚至不大像是正经工作的奴隶。
他从内兜里取出了一条金质的奴隶细项圈,嘟囔了句什么自己戴上,这是好容易才兑出来的人情。
吊牌上的小字说得相当五彩缤纷,
【假如我跑路了。请抓住我。如若你将我归还给了我的主人,M. Antonius,你将会得到一份奖赏。】[4]
为什么要踯躅于此呢?他想到,绕了一大圈,该做的,不该做的也做了。难道他不想像其他自由民一样,一得到自由就乘着海船从罗马飘摇到希腊飘摇到北非,自由自在地悠闲游荡么?
还有他在那不勒斯海边置下的白房子。[5]可以下水泡一下,划一会儿船,参加一个永不停歇的派对。但堆砌奢华只能带来太多的无聊。去沙海找将军玩儿呢?荒无人烟,阳光刺眼,将军又自顾不暇。或许赛维林在亚历山大的老房子还在那里……
或许是因为还有执著于此的东西。更或许是,不得不执着于此的东西。哪里又能得到真正的自由,真是为难呢。
好容易觉得一切告一段落了可以闲下来一段时间,现实就一脚把他踹起来飞得好远。那怎么办,一轮博弈游戏下来,他手里赢了个多少人求之不得,避之不及的,嗯,定时炸弹。在这种时候他会对自己的想法感到嗤之以鼻,难道他真的希望热切地参与到他们低智反智的、孩童般的日常生活中去么?像一帮可悲的无花果叶片一样,在空中无意识地随风扑腾,翻滚,颤抖,最后落在地上并入一堆废物?
继续疲于奔命咯。
他为今天挑选了一件对于他这种人来说格外保守的chiton长衬衣,现在他们是叫它tunica了么?软糯柔和的东方风格,女了女气的。[6] 他借着池水的倒影将肩带下拉到了一个危险的角度,将掉不掉,稍微抬手就会恰好掉落下来。
这般值得停留欣赏的美景被一阵急促的咳嗽声打断了,接下来就是熟悉的动作:抽出手绢掩饰住含在口里的血。吐出来?咽下去?没什么两样的。
对于这种剧情发展桑德兰唯有苦笑的份儿,好像此间梦境没有什么不是和现实应和好的。
他年轻时候的影子在下午的暖光中夺目而易逝。桑德兰觉得下一秒钟,一道直射的强光就可以将他精心编织的氛围隔断分裂,连同他的身影一起击碎。
周围的稀落的人都在忙于自己的事情,好像他和他一样都不存在似的。
少年不在意地蘸了蘸唇角,很快毫无公德地将手帕在喷泉里清洗干净拧干收好(不如说是毁尸灭迹),神色就恢复如常了。他阴郁地想,从好的方面来看,至少他这次没将肺泡咳出来。
小脸上溢起不健康的红晕,这病病殃殃的小样儿并不好看。或许是为了弥补,桑德兰一脸黑线地看着他自己将腰间的衣褶往上折了折,露出了纤细圆润的小腿根部。
一只祭品羊,两只祭品羊……
在他最出格的梦里,他都没想象过他居然还可以做出脚丫踢踏着踩水的模样。这个侧卧着的高难度动作营造出一种S形身段曲线的视觉错觉。
这是第几次了?两个月中第四,还是第七?为了做出恰当的铺垫,要只留下一个纤丽的背影,一个不经心的侧脸,甚至一段若隐若现的留香需要下多少功夫。中间他为了显示自己没有那么着急得不择手段,还错过了几次。他目测着阳光打在地上的阴影的角度方向,也该差不多了。
他真的不喜欢等人,所以往常会姗姗来迟一点。于是,为了完善利用这段碎片时间,他将这条腿收起来,那条腿抬起来伸得笔直,权当是练起了劈叉。[7] 假如不是不清楚他察觉不到他的存在,桑德兰甚至怀疑另一个他是不是在故意恼他……
……六只祭品羊,七只祭品羊,到了。
一大帮带着紫绶带的祭品羊大人们陆陆续续地从罗曼努姆的方向行进过来。他们多多少少气宇轩扬地秃着顶,功标青史却又中年危机,雪白外袍在鹅卵石地上滚着泥,不带走一片云彩。
一大帮家世显赫,吃喝玩乐横行霸道的寄生虫。
什么时候他曾被预计是他们中的一员。那是另一个世界了。人们走走停停,他就坐在那儿。桑德兰下意识地扫视着面孔模糊的人群,希拉应该不远了。事情到了这种程度,他居然还在精神空间里为它留了位置。
刚刚散了会,有些大人想着回家吃什么,有些大人想着回家把谁吃了。有些大人字面意义上想着回家把谁吃了。
其实吧,哪里有白来的午餐;哪里有白来的情爱。
他当然晓得它这种类型的天上跑的,水里游的,什么样的没见过。不过还是要琢磨着贴近对症下药。仔细想来,它大概会喜欢看起来清纯可人,仔细又不大清纯可人的。
少年微微动了动,找到了他那张小脸最美的角度。好极了,侧逆光,吹弹可破。
城池一样的男人,流水一样的男孩儿——谈情说爱中的。两个男孩儿,三个男孩儿,都是复数。似水年华,每个都像水流一样,明晰透彻(肤浅见底)。
这次可能要是像血流了。这样也好。
桑德兰注视着他的影子精准地抬起头,小鹿眼睛脉脉地凝视——错,钉死了希拉。
一双血红眼睛终于再次与他对视。毫不遮掩的,猎手的笃定。
这就对了,他确保了他是在人群中第一个被看见的那个。
一个稍纵即逝的念头。
假如这瞬间可以无限延续就好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它也开始多情善感起来。
毕竟是在扮演猎物,祭品少年先将视线移开了。他略带羞涩地笑了一下,露出了两只不尖不圆的虎牙。他不再幼嫩了,却还要给出一种天真的错觉。
他动了动藕粉色的嘴唇默念,让我们活着,让我们去爱。太阳可以升落浮沉,但我们,当我们短暂的日子尽了,必将沉睡在永恒的夜。[8]
一阵微风很给面子地经过,并非脂粉气。这个坏孩子事先焚了乳香,混合着薄荷,薰衣草皂角和别的什么。不过希拉先辨认出的,照旧是清淡干净的血味儿。它口舌有些麻木起来,喉咙下意识地吞咽,燃起一道纤细的火焰。
“多少钱。”[9] 他寻摸的新主人直接问。如果有些人自己都明确表示了不尊重自己,它何必要去尊重他。
他眨了眨眼,炫耀着日光下浅金色的浓密睫毛。“您说是水?” 他当然巧笑嫣然,装作不懂。怎么连个今天天气真好啊都吝啬,真是的。
但是他得到了一声轻哼。“多少钱。” 希拉耐着性子重复了一遍。
他用打理好的那一边的手肘支起身,肩带滑落,完成。
他感觉得到暗红色的视线跟随着他,彬彬有礼地欣赏节目。
男孩儿懒散地起身走到水井边,拾起水瓶,不忘低低弯下腰,lordōsis,完成。
他将刚刚溢满的水送到了他身前,眼睛发力形成两只弯弯的月牙,轻声在他耳边吹气,“为了您?不用钱。”[10]
“那不谢了。” 它居然把水接了下来,转身走了。
第二个工作日一早他就从掮客那里得到消息,将军将他转让给了勒托里亚准参议员。十二万塞斯特帖姆,比他估计得稍微高了一点。[MOU2] [11]
...Ιρις...
离长老院集会两小时,卡特琳坐在梳妆台前。她一点儿也没兴趣涂上那张美艳的假脸。
“今天不了。” 她挥了挥手让女官把鲸骨撑和她那件标志性的火红礼服撤了下去,后者无声地将那套军部制服取了出来。还是梅丽莎最了解她。
既然他们要让她下台,她至少要让他们下不来台。
她将头发束在脑后打了个结,这还是她们一帮二战被要求替补上阵的女官在军中匆忙研发出来的,再以前当然不存在这种问题。开玩笑,只有那种不得已的时候他们才会将她们放在最危险的位置上。让女性军官从后勤的繁琐中解放出来,只重新置于狙击、殿后等等无人敢要的位置上。好像这样就可以批量化地损耗最小化,利益最大化似的。这么做他们还意在重新洗牌,重塑维图里军部血族配置的“纯净”。
她就是要向他们证明,他们估计错了:大错特错。
当她在全身镜前别好最后一枚勋章时,忽然想起上次这么穿,还是十几年前算计好时间,要上台前夕搞的面子工程。她骑着前任简妮特,佩剑到长老院礼堂册封上任。真是巧了。
时候还早。她坐在议事厅她那把定做的椅子上,不紧不慢地抚摸过扶手上的纹理沟壑。当时为了这个她还和他们吵了很久,摄政长老需要有与她名分相称的椅子。长老院的下人在这种时候倒是破格地效率很高,早早将她的椅子从搬到了王座一边。
她望向拱顶和透过天窗俯视的宝石蓝月亮。之前一心向往的金碧辉煌现在让她想吐。
太令人失望了,她擅长制造鲜血而非专情于这把椅子。头顶上的蓝月亮打了一个侧光,照在她一边脸上,突出了高颧骨和坚毅的线条。
门开了,没有必要宣报。她就这样坐在这里,等他们不紧不慢地走过来。
为了以防正式登基前的不测,路易斯下意识地站在了亲王肩后两步处。虽说这种事密党这么多年并不是没发生过,就凭他?
卡特琳娜很到位地笑了。不需要初次见面就撕破脸,更不需要给一帮梅苏塞拉看笑话的理由。
按照卡玛利亚律法:政府领袖先给氏族首脑行礼;按照维图里律法:世代低下者应当先给长辈行礼。
需要做个表率(其实是懒得让反对派再费心提出来),她率先走下台阶,身着制服,将一只脚放在另一只后面,稍稍欠身,一丝不苟地行了屈膝军礼。
卡特琳娜颔首,几乎不可察觉地抖了抖肩(路易斯同时往前移了半步),片刻后,展现出一个微笑。
“夜安。陛下。” 当然不是“我的陛下,” 她由衷看不起这种毫无功勋,资历为零,全凭着爸爸的好姓氏上位的家伙了。
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这个年轻的继承人,虽然和上流社会的诸多小少爷二世祖一样衣着靓丽,举止得体,可那只是个孩子呀!他们居然为了这把椅子,卡着密党的年龄法转变了一个孩子。她为他们的不择手段而不齿。
他大方地回了一个鞠躬,甚至还笑了一下。“夜安,摄政长老殿下。”
“Grace is perpetual (典雅永恒)。” 要她说,整件事一星半点儿也不典雅。
“Grace is perpetual.” 亲王走到长方形桌前,慢慢在加了增高坐垫的主座上坐了下去,才学着说了一遍。这种对氏族的集体奉承得到了应和,其他几位顺势乌央就座。
令人不安的肃静。路易斯似笑非笑的表情让她想掀桌撕了他那张死脸。卡特琳娜慢慢把一口气吐出去,保持冷静。
抢在投票前,查尔斯公爵不阴不阳地恭维了小亲王手上晶莹闪烁的婚戒。
“戒指不错,” 威尔士领主刻意顿了一下才接话,“小陛下。”
“真是好样的。” 这句话她冲着路易斯说。她记下这一笔了。卡特琳娜转头向通报员妥协,“传埃德加。”
“埃德加·海依·卡莱尔·维图里-诺丁海姆IV到。”人家早就等在议事厅外面了。
血奴又搬来了一把早已准备好的临时椅子,右手边乔奈尔起身将席位往阿格纳身边挪了挪给人家腾出位置,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伤害之余加上侮辱,那小子一脸娇羞少女样,在桌子下面牵住了埃德加的手。
卡特琳娜快速的转着脑子,说实话,比起在桌面上和几个老不死的尔虞我诈,她更愿意伸开翅膀去和魔党火并去。好了, 埃德加去吃新亲王的软饭了,这意味着新的长老任命需要投票,需要全票通过。这意味着,假如她还想暂且保住她的位子的话,她就得让他过。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就得听话地给他开一路绿灯。要想打破这个圈子,收获他们垂涎已久的空前的好结局,他们别想不给她一个差不多的好结局。
好在元老会的议程设定权还在她手上。
“我看不成,这个任命是史无前例的。” 阿格纳代她说,她也面露难色。从高贵者朱博尔开始,到卡帕多西亚那帮近亲繁殖的败类,走后门都是上不了台面的,没有哪位高贵的大人,甚至哪位女皇会把男宠拉来搞政治(她显然并不认为乔奈尔算是男宠)。
路易斯立刻放下茶杯“噢?” 了一声,“这个任命是史无前例的?” 他挑了挑打理得完全对称的眉,“在月落城?” 在极少数情况下,就连报纸社会版都可以拿来当黑天鹅用用。真是千算万算不如赶巧。假如不是实在不好这一口,他都想给勒托里亚亲王妃往府上送上一捆花。最好是鹫尾加上山茶,整它一个战后一家亲。
她将嘴抿成了一条线,哪壶不开提哪壶。一想到那场办砸了的刺杀,和一个一个收了好处都不好好办事的混蛋她头更疼了。看看,不及时把那个伪鸟人弄死,到现在人家还变着法儿给她来找气受。不过现在她没时间操心那个该死的主教了。
“在维图里,似乎是这样。” 就算这件事能成,他也不好直接做出表示。何况由新党直接控制的伦敦城,并不是他想看到的。查尔斯拍了拍手,把早在一旁候着的维图里法务咨询支了过来,后者叫助理推上来一车以往判决文献,刻意地咳嗽了几声,开始背书。
“回长老,最近的一次先例可以追溯于1453年末,前皇室首领,王位觊觎者埃莫里特·卡帕多西亚殿下向刘易斯·德·费尔南德子爵求婚并签署永久伴侣契约,触发宪政危机。
维图里各执政官与长老院反对这一婚事,并认定民众无法接受一个异族同性且世代低下的梅苏塞拉将成为密党皇后的现实……
最终在与历届维图里长老会,协同卡玛利亚议会协商后,立诏宣布退位……”
在平板单调的背景音下,几位大人不紧不慢地坐着喝茶。
半小时后,“这就够了,” 总算是听得心满意足,公爵叫了停,“菲尼克斯,谢谢你的意见。” 大法官嘟囔了一句“我的荣幸”,就带着一帮喽啰从这个是非之地早早撤了,他可没义务在双方交火中被殃及。
“摄政长老殿下,我想知道您怎么想?” 亲王终于插了一句。
这个摄政长老说的还真是意味深长,年纪轻轻不学点儿好的。“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 他们松口了,她就必须松口。“于情于理,历来族里的规矩也没说不行。”
随你们便。阿格纳耸了耸肩当是表态。亲王的姘头照着以前的规矩别插手到军部来,他想插谁还是被谁插管他什么事。
“那我们投票?” 路易斯一脸假笑,用商量的口气说。
“那我们投票。” 没什么可商量的了,她面无表情地念道,“在座同意埃德加·海依·卡莱尔·维图里-诺丁海姆IV作为亲王配偶升为维图里长老的,说Aye.”
“Aye.” 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
只有在这种时候他们算是团结一处的。“看样子全票通过。” 她还是照着台词往下走,侧眼瞧着角落的书记马不停蹄地挥笔书写历史,“那么,埃德加,我代表长老院欢迎您的加入。”
“谢谢,” 他站起身来,悦耳的男中音开始了用词精准的例行发言,“几天前,我与我所爱的男人携手签下了伴侣契约。我的第一句话必须是向他宣誓效忠。我全心全意地做这件事。
我们做了这个决定,这是我们一生中可以做出的最严肃的选择,因为我们唯一的想法就是什么,在最终,才是对所有人最好的。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长老院的周全考虑和成全。在我和长老院成员之间,我和内阁之间,从来就没有任何律法上的区别。我是在我父亲的法学传统下长大的,我绝对不会允许任何这样的问题出现。[12]
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新的亲王。我衷心祝愿他和您,他的公民幸福安康。该隐保佑维图里;该隐保佑亲王。
托您的吉言,我将尽自己最大努力不负众望。” 新任长老说着漂亮的官话,在桌面上回握住亲王的手,两个年轻血族相视而笑。
...Ιρις...
“小姐,地下室的东西?” 敲门进来,梅丽莎用问询式的眼神说,这时候她家太太一点就着。
“留着它们。” 她深吸了一口气。她还有二百年能准备回来。
卡特琳娜倒在很快就不再属于她的古董床上,她在这里代历任亲王接见了多少密党高官才稳住了维图里的疆域。光线很暗,她就想这么躺着,再也不起来。
“梅丽莎,你说我该怎么办?” 她低声像是在对自己说。
“像您一如既往的那样?” 她在床边坐下,帮小姐拆开那个依然纹丝不动的的发髻。
“没错,就是这样。” 她直起身来,开始和女官一起打点随身的物什,一点书信和剑。她把她其他所有东西都留在这儿了,甚至是她的首饰。真是好笑,最后来来回回,只有两个箱子。
她继续往前走,因为她知道,当她停下时,就会终于发现自始至终,她什么都没有。
他们什么也不会让她留下。
作者注:虽然伊丽莎白一世是显而易见的原型人选,卡特琳娜其实是我们对沙俄的凯萨琳大帝的角色研究。当然是做了演绎化的改编,凯特比她处事理性,下手快准狠多了。当是同人看就好^-^。
[1] 国际象棋术语,指在终局阶段两只主教用占领的对角线囚禁住敌方的国王。
[2] 这是对于Proverb 27:18 不正经的无授权翻译。
[3] Suetonius, The Life of Augustus, 26.1.
[4] 改编自一个奴隶项圈的铭文, CIL 15.7194 (ILS 9731)。
[5] 据说罗马城有钱有闲的大人们最喜欢去那不勒斯海边度假了。Seneca the Younger, An Essay about Peace of Mind, 2.13.
[6] 罗马用语里东方(Greek East)指地中海东部的近东和希腊世界。当然,这并不是说远东风格就不女了女气——哦不——温文儒雅了;)
[7] 在当代,这个伟大动作的代言人好像是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夫人。
[8] 桑德兰在引用Catullus, Poems, 5.依旧是作者的松散翻译。
[9] Quantum vis, 原意更贴切地说是 “你要多少。”
[10]Ut te gratis (For you, for free),“为了您,不需要的?”
[11] 虽然共和国末期货币估值是个兵家必争的命题,作为参考,蓝领平均工资大概在每天3-4 Sesterces,一百万Sesterces可以在帝国初期买下一个参议员席位。简而言之,希拉给多了。
[12] 部分参考了爱德华八世1936年的退位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