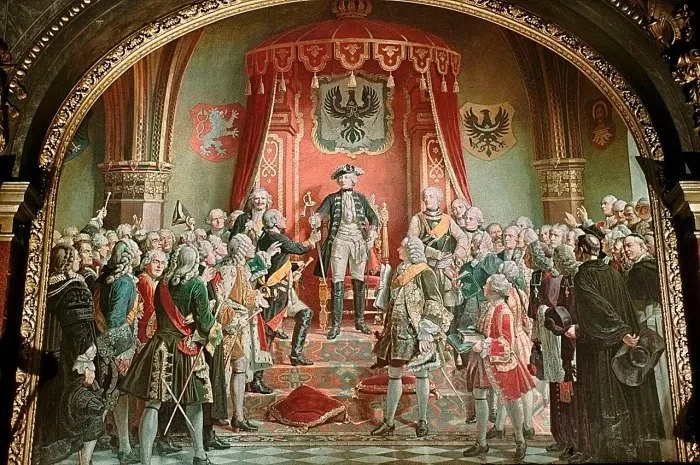Scorpiris Schemata 蝎鹫尾图式 第二十七章 时间的琥珀
第二十七章
Amber of Time 时间的琥珀
主要坐标: 月落城北翼,希拉·勒托里亚II的深红庄园,1762。
Moonlit City, Northern Laetorii Territory, Crimson Hill of Lord Zillah Laetoria II, 1762.
月落城北翼,巴托里伯爵庄园,金蔷薇宴会厅,1760。
Moonlit City, Northern Laetorii Territory, Villa of Countess Bartoli, Rosa Foetida Hall, 1760.
克里特侯爵府,北普鲁士,1762.
Markgräfin Kret’s Estate, Northern Prussian Kingdom, 1762.
建议配乐: 第一幕 Ramin Djawadi, “We’ll Meet Again”.
第二幕 Villa-Labos: Bachianas brasileiras No.5 for Soprano and Cellos-Aria (Cantilena), by Milos Karadaglic, Anna Prohaska.
第三幕 String Quartet in D Minor, Op. posth. D.810 “Death and the Maiden”: II. Andante con moto, by Franz Schubert, Jerusalem Quartet version.
...Ιρις...
这是一个很安全的梦,假如梦可以用安全来形容的话。
在梦里,他变成了一只原木拼图,作为一个娱乐装置被希拉握在手心里反复把玩,打碎又重组,最后成了什么赏心悦目的玩意儿。
它一边玩着,一边在一个marqueterie精工镶嵌,充满了金属质感浮雕的场景里散步。它“被分尸的地图” 被施加了什么药水或是咒术,一片一片悬浮在身前,匀速相伴着走动。
也是,但凡药水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它在闲暇时期构造,不,发现并且妥善解决了诸多问题。然而这些问题仅仅是延续滋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反复分支,接连不断。
远处偶尔传来失格和弦的旋律,隐约可以听出来是同一段,不同的解析。它也不怎么说话,只是一味断断续续地向前走去,偶尔停下来,伸手从半空中拣出一块,与似乎并不相关的另一块拼接。耳边十二声部的管弦乐组成了一道拼图游戏,如何拆解重组,隔断解析这繁复不安的乐章,也不失为一种消遣。[1]
它们似乎不是唯一的访客,偶尔会有人,或是别的什么,从交叉的岔路和两边数不清的门出来匆匆地擦肩而过,有时候希拉会,像希拉一般做的,干脆抽剑将不顺眼的解决了,血溅在拼图上。
有时候它只是任他们路过,好像种种选择并没有什么规律。
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的面孔却依然都是模糊不清的。并不是因为记忆超载,而是因为他们全不重要。
就算作为拼图状态,桑德兰认为希拉能第二眼看透他:这是让人极度不安的。没有人想被谈得上轻而易举地解析透彻。他在目前的阶段早已经失去了进一步了解希拉的意图,却只能拥有对此无可奈何的权利。不但如此,就连这种权利,都是别人飘飘然下放的。就算是现在,他对于上述这三点依旧无法释然。
这时候他先前的猜测已经逐渐明了了:由于建筑群占地面积过广,很难从刚开始就发现,他身边似乎永无止境的走廊是环形的。极尽纷繁,密不透风的闭环。
当希拉在极少数情况下陷入回忆时,它并不希望再次被卷入一栋栋灰白的精美坟墓,残垣断壁和灰烬中。它宁愿被时间的海市欺骗:当它以为在前行时,实际上正在不住移动向过去。
这让人不禁思索是否会真正陷入其中:时间这个人造概念从有序越过他,势不可挡地涌向无序。全然错位。
”我想你知道,我施力在试了。” 我希望你也能试一下。希拉单刀直入地说。
您没有发现我也在尝试么。“我之后会尽量。” 到这时候了,它还想让他怎么样?是天天同它一起外出狩猎,还是集结军部,一统月落城不成?想到这里,他轻轻笑了一下。
好像这一瞬间他断裂得很厉害,不过这终归无关紧要。
“那么从现在开始,你无需再听我的了。” 它有些无奈地说。自始至终他都没有真正顺从过,不过其中引人入胜和让人忍无可忍的成分几乎一样多。它们本来可以一直这样下去。
他听出了这种命令语气的潜台词,勒托里亚有侵入他人梦境的天赋么?不过继续执行之前的命令就够他受的了。他不同的碎片打了打转,缩成了一团尽量远离他主人的手,“或许我应该说’谢谢’?”
“大可不必。” 它同样略带讽刺地回答,顺手将他抓了回来,继续肆意拼装成它预先设想的模样。它下手很轻,却相当毒辣精准。“我手上有个外派的职事可以考虑一下…...”
拼好了,他变回了人形。穿着标志性的高领衫,教士,或是血族。
“这样啊。” 桑德兰平静地回答,就这样好了。
他忽然感觉,希拉在下一秒确切地想杀了他,或者亲吻他。但它并没有这样做。
最后,希拉伸出了臂弯做出邀请状,“现在,陪我走一会儿。”
他不言,伸手环住了它。至少这个他目前还是可以做到。
他们并没有接触到,却可以互相感觉到肋骨间的肌肤。
“就这样好了。” 他退开身,只能这么说。
“就这样好了。” 它同意道。
他在这儿第一次专注地看着它,深邃眼窝打出来的、散不去的阴影。不知道它在思索什么;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想的。
好在桑德兰大概可以确认,这是决计未曾发生过的事。是这样的么?
...Ιρις...
安排一场不见光死的“舞会”是一门学问。尽管请柬一发,俊男美女一进门就大干快上的想象非常诱人,后勤怎么布置,血酒怎么供应,人类血奴要捐多少,甚至烛台光怎么打都是优先需要考虑再三的。
红月7点:这不,伊丽莎白夫人正插着纤腰,亭亭玉立在舞厅正中指挥交通。今晚的主题是“中世纪牧歌”,女伯爵正穿着乡野村姑的底袍指点江山。与其说是村姑的麻布袍,不如说是BL(路西法的飞吻)旗下助理设计师对于村姑的麻布袍的一种奇幻想象。那件浆得雪白的亚麻长袍像抹布一样皱皱巴巴的,裁剪技巧性地强调了脖颈之下,开衩又几乎开到了跨根,显而易见地优化了功能性。
不,这当然不是对于某前首席摄政长老家世背景具有针对性的点评。
为了给丰收舞腾出空地,桌子都被搬到了一边,宴会厅零星放置着几束定制的柔软稻草,当然是为了贴合一种原始的,狂野的意象。
就连原本装点着壁画的华丽墙面都被细心地覆上了挪窝原木,吊挂着新鲜花藤。零星散落在立柱上的金玫瑰浮雕被人用临时染料喷成了灼目的鲜红色。这种引人入胜的景致衬着火红的剖光晶石地板和一簇簇稻草,却显得有些失真了。
被征用的舞池边缘,四个衣衫褴褛不拘小节的“流浪艺人”正在有一搭,没一搭地对着和弦。这是她托了朱丽叶塔的情,重金把人从魔界皇家音乐学院拉过来的。这几位真真来自16世纪末的乐手特意准备了几首轻快,悠扬的安达卢西亚小调,还很给面子地把不怎么乡野的竖琴替掉了,导致乐曲节奏从欢快转向了跳脱,不过谁在乎呀!对于宾客来说,被邀请到场了,玩儿得开心才是最最要紧的;对于伊丽莎白来说,这是装饰性的恶趣味。
红月9点:中古风格的实木长桌上铺满了美酒佳肴,之间点缀着鲜艳欲滴的新鲜水果,虽然没有人真正需要它。金色落地窗关着,刚刚从花园剪下来的,用水晶瓶喷上露水的鹫尾花在她风系法师闺蜜巧妙的 “风起云涌 (טורנדו)” 下匀速微微打着旋。女主人走上前,用审慎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中心装饰品,伸手稍微将插花整理了一下,管束地她们更加对称了。
她身后不远处一座马厩戏院道具里,二十几个精心挑选的人类血奴被拿铁链锁在一边,她们被清洗干净,不施脂粉,掐红了脸蛋,揪乱头发,套上了配套的麻布裙。她们被老鸨/人贩子许诺了每人三个法兰克,对自己的命运浑然不知,充满期待。
伊丽莎白伯爵在月落城出了名的出手大方,就连这些一次性用品都成色上好,为了取悦某些大人的情结还点了几个“村姑处女”,作为特殊照顾。前几天还紧跟流行玩儿个什么“抽个奖”之类的,现在战后经济不景气,就直接明码标价给了几位预定好的赞助人。
银铃轻响,镌刻着繁茂花枝的大门被从外打开,穿着款式简朴,布精良的青年和伪青年陆陆续续地走了进来。音乐响起,却成了怡人的背景音。他们用无懈可击地礼仪向女主人嘘寒问暖,又三五成群地在大厅里混在一起,拉起了关系。
对于魔党诸多野心勃勃的青年俊杰来说,凭金主,政绩,甚至才华资历混到本家的下议院,军部中层不算什么,要被邀请到伊丽莎白夫人的宴会间,那才真正算是成功了。
所以伯爵每个社交季订正名单时都格外小心,除一般的老面孔名流不提,非灼手可热的商政新贵不请。因果关系滚雪球似的一混淆,宴会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名流和名流热情地打交道,最后不算是名流的也成了名流。
有时候他们喝酒,有时候他们跳舞。由于勒托里亚高层男女比例严重不平衡,没带着女伴或搂着血奴的,同僚和同事跳,兄长和弟弟跳,父亲和儿子跳也稀松平常(大法官小鸟依人地搂着汉诺威领主,跳得很是开心)。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幸活着跳过乡间小调,乐队还是转向了精简过的华尔兹舞曲。
乐池的前排,有人刻意不踩节拍,手持打包自带来的骷髅傀儡,自得其乐地跳起了别人跳不来的塔朗泰拉。那看不出年纪的“少女”穿着红底天青石蓝围裙,腿部动作跳出了花儿,舞步清纯、优美又热烈。朱红裙摆翩然打着旋儿,带乱了周围人的节奏。由于伊丽莎白从那无可挑剔的纯金长发认出了是拟态的普鲁斯特·瓦萨里阁下,索性任他/她去了。
舞会永无止境,鲜血永不干涸。配合着流水似的青年血族。
红月12点:不过反复寻摸人换人并不是长久之计,“马厩”对面的半开放式小厨房灶台上慢火煮着当下时兴的“红色巧克力”,不时有小手握着木勺上前搅上一搅。 炉火边移了歪斜站着几个她家目前的常驻人口:罗塞蒂,爱洛奇斯,维纳斯,宁芙,芬尼,咪咪,阿多尼斯,纳西索斯,海雅星斯,赫拉克里斯,泽维尔和小吉登。一群年轻貌美的孩子戴着小红果花环,纷纷穿上田园与十二家族主题混搭的服饰,上紧下松,脸颊上印着人类特有的红润光泽,嬉笑着准备盛情待客。
或许算是内部笑话,小吉登·瓦萨里被套上了议长标志性的灰呢子外套,而诸位的新宠泽维尔·勒托里亚则穿着的教士常服。那高领袍空虚得很,被沿着大腿根部被裁短,刚好露出两只光滑纤细的奶白色长腿。男孩子在两位兴致盎然的大人身旁腼腆地笑着,掂量着今夜光是小费,就能赚个囊中饱满。不像他上家,伯爵夫人是个很好的人,并不屑于去揩他们的油水。
然后他就被推倒了,顺势用最标准优美的姿势仰卧在像云朵一样的稻草上,轻轻“啊”了一声。
烛光暗了下去,宴会才正式开始。前半晌还衣冠禽兽的大人阁下们,簌簌地成了衣冠不整的禽兽。
后边儿也不知是谁咬开了血奴的手腕掐着开了一座“香槟塔”,得到了与会众人的一阵唏嘘,又干脆直接将那可怜女孩儿扔到草垛上,急匆匆撕开衣布裙,从两个方面同时吃干抹净。周围的喝彩声更浓了。
落地窗外的天台扶手上,停着两只蝙蝠。不,它们当然没有在做什么应景的事,只是在观察人们。
“哼哼,阁下还安好吗?” 那只毛毛草草的小家伙旁敲侧击,它居然借主人被发配回它老家后也不摸鱼,不日学会了双关语。
“或许你可以说服我。” 另外一只不可置否。
“假如这座城没有爱,城里的人活不下去,这座城也不可过活……” 蝙蝠也不知照搬了什么罗曼蒂克的桥段,哽咽着感伤起来,“这包括我对月落城的爱;主人对月落城的爱;我对主人的爱。” 它爱了半天,无懈可击的语序从咯吱咯吱降维到了近似哀怨悠长的鸟鸣声。可惜再怎么呐喊,屋里一群类人生物都捕捉不到。
哪壶不开提哪壶。“哈。这些幻想!多么荒谬!” 特洛伊沦陷的时候,它正在临时的家里苦读。妄想着配出得以解决时间带来的一切问题的药剂,虽然最后它配出来了,却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它佩着镂空红石头银环的右爪突然更疼了。
“阁下对这座城的爱,使他变得盲目。因爱而生的错误——也该叫错误吗?” 这只变种蝙蝠奋力使起思辨思维,它往后跳了一步,勉强支起半拉翅膀行了个大礼,“请再给咱家一个修正失误的机会。”
它冷笑了一声,扑翅飞走了。
蓝月4点:伊丽莎白永远是“那个女人”,好在她早已经习惯了。
要乐子还是要名声在以前可能是个问题,然而,现实状况是既没有乐子,也失了名声。
罢了,想不明白的事,不去想他。她用侧卧在贵妃榻上的姿势,懒怠地卧靠在稻草上。
她就这样躺着,观察和感知着周围的人和事。说她耽于享乐也好,说她懒怠散漫也不是不可以。
可以舒服着来,何必那么费劲儿?
比例不大和谐的大红月亮,顺着落地窗的缝隙漏了进来,好像她苍白的巴掌脸上浸染了血。
她装点着金蔷薇的宴会厅并不是月落城最阔气的舞会厅,却是唯一一个一转角就能走到隔壁人造温泉池的。一种熨帖的策略。她用余光打量着两个青年俊杰无视游戏规则,将点心架在中间“外带”,正准备浑水摸鱼穿过透出水汽的珍珠门帘。伊丽莎白笑了笑假装无视,今天团队又要拿着软布和消毒试剂,尽心尽力地洗涮浴池了。
虽说她搞了这么多年,当然明白这种大型集会就像是婚礼,鲜少有一帆风顺的。话是这么说,她却要打点到尽量卓越完美。为了物尽其用不浪费,侧厅里甚至坐了个人类科的门诊医生。她早年为了省事,还自己学会了怎么给缺手断脚的人类缝缝补补,可惜这在正式场合是“不够淑女的”。
谁家大少为一名妙龄“山村处女”验明正身之后,扥着鲜嫩的脖颈咬破动脉开始了大放血。他大快朵颐了一会儿,觉得一个人喝不尽兴,又支使染着夸张的红发,不着寸缕的罗塞蒂·维图里将巧克力奶锅拿了过来接着,一勺一勺舀在小姑娘身上给大家伙儿分了。这个慷慨阔绰的举动赢得了大人们的一片掌声。
正是这个当儿,就有贵客不请自来了。因为是贵客,穿着希腊小白袍扮酒神的小门迎眼尖着,并没有将这个穿着三重正装的家伙拦下来。
女主人一手端着血酒,一手引导性地闲闲搭在跨上。
他居然将潘城的苦差事谈成了,这怎么说都有些出乎意料(大概有些人又动用了千丝万缕的隐秘关系)。不过呢,她觉得偶尔的这些误差值还是蛮有趣的。
还能是什么,互相保留地交换小抄呗。打着巧劲儿,用月落城的糟心势力制衡那些数世纪死宅的潘城贵族,也亏圣安东尼想得出来。
也不知他们清不清楚,几方与那些久居深宫的大人们的关系从来不是规整划分的。暗通款曲的照样暗通款曲,躁动不安的更加躁动不安。
这么说,终于要有新面孔了呢。或许是说,重识老面孔。伊丽莎白对不久的将来的乱象表示由衷的期待,毕竟在她的酒局,当然是越乱越妙。她从胸前的暗袋里抽出配套的折叠羽毛扇子,凑在烟粉唇边轻轻扇了扇,遮住了狡黠的笑。
舞池中的孩子们还跳着华尔兹,舞池外的还卧在一起翩翩起舞。伊丽莎白在人堆子里,轻轻打着自己的拍子。衣布裙的内搭上衣解开了两个扣子,坦胸露乳,却坦荡得十分从容,分寸感十足。
她特意绑了一个麻花辫,海德里希揪住了她的麻花辫。
黑灯瞎火非常暧昧,周遭都是衣衫褴褛的曼妙肉体(小吉登同款的外套已经被铺在了身下),逢场作戏谁不会,她只顾娇俏呻吟着不松口。
果然他耐不住了,采取了一个经典的古典式姿势覆身而上,腰间耸动着,在她耳边深情低语,“贝拉,帮我。”
她忽闪着睫毛,红眼睛中含着水,恰到好处地,香艳而不色情。
谁想做他的“贝拉”。也就月夫人那种专业的,才能忍住他一高兴了,就上手将情人往死里打的坏习惯。要不是隔三差五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她才懒得叫上这种不知趣的家伙呢。
她单手抚上勒托里亚议长线条锋利的侧脸,同样深情地:“我的阁下,暂且不用担心。”那边还有一堆要优先解决的事儿。例如说,亲王和他拐来的亲王配偶不和,是氏族里暗搓搓流传已久的小道消息。希拉绝不会卡在这个紧要关头换人的。“您的问题,很快就会变得不是问题。” 顾忌和顾及都有些多余了,要她说,缺失各方面经典的感情或是利益上的维系,那一对儿从一开始就不能长久。
“真的是这样?” 根据他们的预测,别说政治阻隔,希拉别直接持剑过来和他决斗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嗯…..” 她享受地将腰后仰,不再答话。不说这是政客赖以生存的敏锐度,而是她作为女人的直觉。她喝了很多的酒,当然要假装醉一醉。
海德里希看她的样子也问不出什么了,就将她在稻草堆上放下,换下一个人上。
很快他们研发了一种新颖的玩儿法:用一个法兰克引诱血奴走到二层半挑空的平台上,然后比着赛瞬移上楼将她推下去。当然,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垂直迎接而来的是薄薄一层稻草,仅仅会摔断姑娘的胳膊或者小腿,在大部分情况下。
然后获胜者即可瞬移下楼享受他的战利品,生死不忌。
作者注:这一幕四个时段的推进灵感,来源于唐纳蒂安侯爵Les 120 journées de Sodome中的分段思路。*摘帽致意*
...Ιρις...
他再次醒来时,端坐在宴会厅里,头顶悬着放得很低的黑水晶灯。
桑德兰眨了眨微干的眼,取出冷藏罐投喂了早已经嗷嗷待哺的“鱼”,却有些心不在焉地琢磨着那封本不应该被寄到的信。
天主给予,正如天主取回。理所应当地。他无意去前往对峙,错过了却有些可惜。
他还很年轻,却已经老了。
桑德兰瞬移回地下室,在白麻衬衫外套了件宽松的黑袍。这让他的脸色显得更苍白了。
他走到穿衣镜前,还是用一层深蓝遮住了令人不安的红眼睛。就像以前那样。
从不详的暗紫色门扉里出来,空气中一股陈旧、腐朽的味道,混着花粉的冷香。
他匆匆走过回廊,提醒自己不去注意周遭景观,或者他对于这些没有什么变化的景致的感受。被厚重黑纱蒙上的画像已经被揭开了,布也没有丢掉,好准备覆盖另一幅肖像。
忽然之间他感到一种错觉:冯·克里特侯爵仍然还在这里,他和全部与他相关的事物。在他一厢情愿地认为有所改变的时候,一切境遇一如往常。
是的,这里不再是他的地方;但是这里仍然是他的地方;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将属于他;然而他并不想要。
身边很近的位置,抱着独角兽的贵族少女向他微笑,那是一幅画一厢情愿地,对另一幅临摹画的模仿。
“小姐姐多可爱啊。别这么古板,这肯定能点亮整个走廊......不嘛,我不听......我就要!”
侯爵不在,夫人叉着细腰满脸不耐烦,半点儿也不高雅!花了这么多的钱,是让这个小丫头这么造的吗?
宫廷画师手在半空举着下不了笔,他端着劲儿坐在画板前,一脸迷茫地眨了眨眼。
他只是宠溺地眨了眨眼,走上前把带歪的花环和鬓角的卷毛整理好,又退开。你想怎样就这样好了。
“还是小哥哥最好了。” 一阵鸟鸣般的嬉笑。“要不将你也画进来?”
他并没有停留。
桑德兰继续向前走去,他终于抵达了中层楼看似漫长无尽的转角,主人房厚重的实木门敞开着,正在欢迎他进去呢。
他悄无声息地短暂停留在了走廊尽头的阴影里,阿比拉德静卧在乌木四柱床一堆靠枕上,没有什么表情,很明显意识并不在此。压抑而惨淡的暗光并不碍事,桑德兰有效率地环视四周,他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寥寥几个在床边围成一道半圆弧,有人担忧,有人认了命,有人呈若有所思状。但凡阿比拉德还在,他们尚能维持一种崇高而体面的表象。可是怎么说?老的已经老了,年轻的太年轻了。
那个眉眼之间生得酷似桑瑞妮夫人的年轻姑娘目中含泪,握住了克里特夫人的手。莎布丽娜·……·冯·克里特眉头紧蹙,用审慎的目光望着她的丈夫。恩斯特大概已经不在了,莱文还套着一丝不苟的管家服,伫守在房间的一角。
好端端站在一旁,头发花白,无法为侄子做临终祷告的枢机主教神色不变地低声喊了他的名字,却念得好像是在叹息。赫尔伯特大概因为十年前的旧事,确切地说是因为他,丢掉了罗马主教选举的资格,不过他并不怪他。
他踏进了陌生的房间,颔首回应,却不免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病床上的人。时间过得真快,不过理所应当。
桑德兰想半跪在床边,牵住哥哥的手,最终却只是不远不近地站在那里。
没有什么变化,也没有什么没变了。
“还知道回来啊。走近点……让我好好地看看你。” 病人神色灰败,声音沙哑。他没能光荣地死在战场上,算是一去不复返的机会。
桑德兰稍微往前挪了一步,室内摇曳的烛光在他身上裹了一层朦胧无暇的光晕。这一瞬间他不再像是人,而成为了某种近似有机的名贵瓷器。虽然是不死之身,却与死者无异。[2]
阿比拉德眼角一阵抽动,海蓝眼睛蒙上了一层灰白的眼翳,褪成了两池浑浊的灰蓝。
他像是看到了鬼,挣扎着坐直起来,面色更加阴沉了。
桑德兰平静地看着他,透过他在看其他的什么东西。
“真是好样的。” 你为什么不早点去死呢?
桑德兰准确接收到了其间的潜台词。真是遗憾,您说是不是?
“我托假赶回来,准备给父亲处理后事,” 他还是选择一针见血地平铺直叙,“然后在墓室里我看到了什么?” 阿比拉德冷笑,本来不该死的,“青白腐烂的尸体。”
桑德兰垂头无言以对,他还能怎样呢。
“您还需要我做其他的什么吗?” 虽然已经知道答案,他还是提出了这个潜在选择。这么多年他已经明白,这种无痕更迭在霍亨索伦及其旁支算是稀松平常。卡玛利亚出于忌讳,还需要取得非直系亲缘长老的血,在魔党这都免了。
干枯的手从抽屉里抓出早已经收回来的银十字架,扔还给了他。桑德兰伸手接住,将吊坠攥在手心里,出奇得轻。一阵低微汽化的声音。
“走,克里特主教,” 阿比拉德用力摆手,“滚得远远地,永远也不要回来。”
“可是父亲——” 威尔米娜上前握住侯爵枯槁的手,没有人意料得到侯爵会在这个时候发病,他们本家再没有其他的男性直系继承人了。她断续的争执却被一阵持续不断的干咳打断。突然中年人的头垂了下去,他挺直地向前倒去,看起来像是被折断了。
他的家人们纷纷发出一阵震颤,之后便是低低的絮语。无视众所周知的事实,女孩儿还是急忙去拉铃,“医生,医生……”,家庭医师拎着包聊胜于无地赶到;被支使到门外的路德教长老终于被请了回来,奉主的名义用油膏点抹他,为他祷告……随后的种种都混淆成了一幅模糊混乱的画面。[3]
然后桑德兰消失了。
两天后,他接到家书宣告他成为了新任克里特侯爵,这是哥哥能给他的最后的嘲讽。
[1] Mark一种现代的乐理分析手段,是叫维也纳拼图么?详见Eggers, Katrin. "Wittgenstein and Schoenberg on Performativity of Music as Method for Philosophy." Word and Music Studies 12, (2011): 243-261.
[2] 这一行桑德兰松散引用了弥尔顿的失乐园。
[3] James 5:14-15, NKJ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