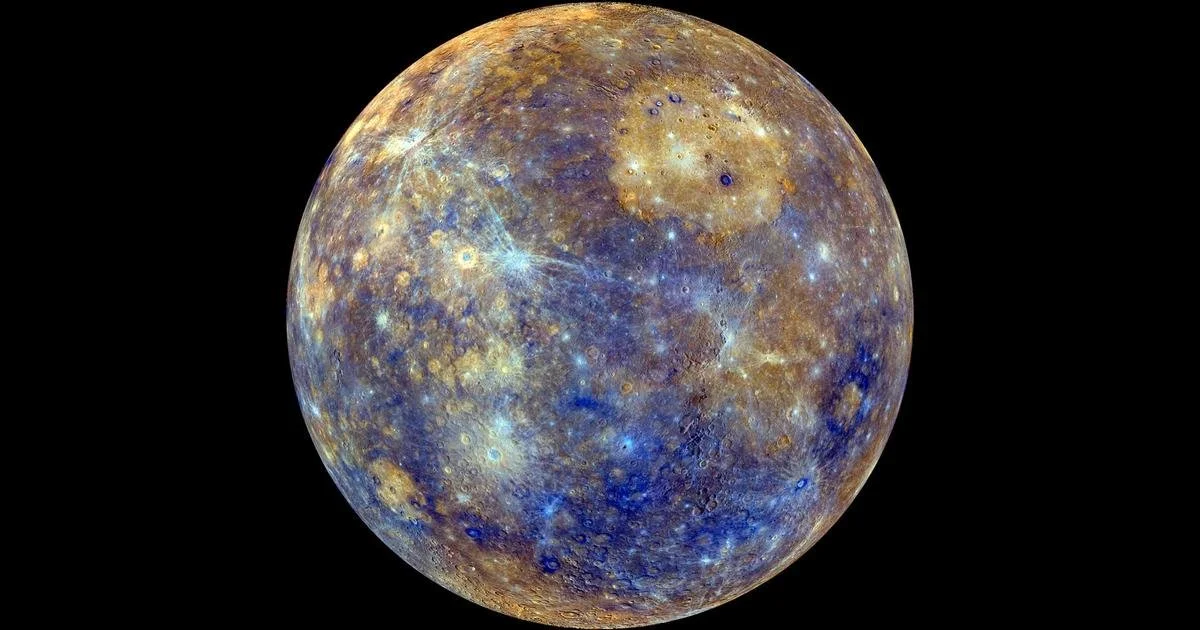Scorpiris Schemata 蝎鹫尾图式 第三十章 渡鸦的狂欢节
第三十章
Carnival of Crows 渡鸦的狂欢节
主要坐标 威尼斯共和国 圣马可广场,1789.
Republic of Venice, Piazza San Marco, 1789.
建议配乐 Peter Gundry, “The Vampire Masquerade” in The Edge of Darkness.
...Ιρις...
吸血鬼?他们是一群忘恩负义、不怀好意的玩意儿…...吝啬、傲慢又善妒。对于制造旧的无聊和新的疯狂天赋异禀。
永生是相对的,一个病态的社会构造。
人们总是认为偶尔扮成怪物十分有趣,而他将终其一生假装自己并不是。扮演自己也算扮演么?为了迎合一种乔装打扮,精心修饰的刻板印象。
他穿着一件吸血鬼的蕾丝衬衫,这让他看起来就像一只吸血鬼。
他的选择的穿戴是老式的,不过这样的措辞当然不适合他披着的令人艳羡的服饰。这些华丽的阶层制服大概也只适合于这种场合。
狂欢节中一部分人为带上面具欣喜,一部分人则为另一部分人同他们一样带上了面具而莫名欣喜。老爷与夫人们暂且趁着实物伪装抛掉那张修辞的面具,而他只是从一张面具临时换到另一张。
他今天有些累了,他应该成为别人。
”面具之城“张开双臂欢迎所有人:西欧和近东的,贵族学者游客冒险家。狂欢节时期广场被纷繁缤纷的帐篷殖民了。望眼可及之处都晕满了声光色,独特而明快的美。真的假的占星师,法师,人偶师,歌唱家,先知和行骗专家熙熙攘攘在同一条街上,欢快地售卖着盗版书,玻璃摆件,手工蕾丝和不可兑现的诺言。
不远处的年轻画师正在将这张狂的全景事无巨细地收入画布上,他决定将这命名为La Serenissima:最平静的海市城邦。他由衷地盼望这一单得以将他的画和他自己打包出售,卖个好价钱。
盛装的人类和奇装异服的什么其他的,不约而同地挂上笑脸,和相识的,素不相识的,陌不相识的混迹在一处翩翩起舞。望眼四处都是明艳得刺眼的颜色,有些甚至渲染进了在灯火下明明灭灭的暗色的河。
谁想在阿尔马科斯跳舞,即使是为了莫大的荣耀?它们可以巧妙地在任何场合露面,而且几乎永远是作为发起人和主人。然而,这种舞会的乐趣就在于可以短暂地泯然众人,成为任何人,成为任何非人。
毕竟天亮时,一切都默认成为了过去。
这是体面的规则,也是恒久以来保持体面的法则。
桑德兰缓步行走在人群中,用另一边的手整理着被海风吹乱的、用真发制成的亮银卷曲假发,并没有什么可茫然若失的。
一个瘟疫面具与他擦肩而过,黑袍和黑色的渡鸦鸟嘴。啊,今天算是什么呢,和他过去见到的还是一个样子:一个具象的、不透明的影子。
“陌生人,过来跳舞。”[1] 它伸出手,完美礼节对它来说就是过场一样简单。
“为什么不。” 白银面具失笑。他特意从子爵的Le Charisme订购了一只风雅的弄臣面具,这是说,假如弄臣可以模仿风雅的话。或许是意在调侃小丑虽是上流社会的常客,但又不属于此,并且时常好奇而婉转地质疑那些不言自明,却又讳莫如深的世情和人情。又或许是,没有什么言外之意。
两人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合礼距离缓缓地打着旋儿, 烛火忽明忽暗,短暂得将每个人照成阴阳脸。
亦或者说,恰好切分成四片面具。泾渭分明地不分你我。
隔着一层银白色的绸缎手套,桑德兰牵住它的手转了一圈,和它贴近,却离得更远了。
他只好又后退了一步,反作用地引它微微向前。
他满是回忆,却不想滞留在回忆里。于是把手松开了,又重新搭回希拉的肩头。
将脸藏在瘟疫医生脸侧,桑德兰虔诚地看天,星图上全是清晰又模糊的名字。
蓝月和红月并不涉猎此处,忽然他再次发现,月光是霜白色。
希拉骨子里是个相信浪漫的血族,那种看似无用的,古老的,鲜血与雷电交加的浪漫,在商标性的虚情假意与昂贵的鲜花统治世界之前,在那种浪漫之下爱人最后一同走向美丽的熵灭。
然而现在并不是浪漫和熵灭的时间,截然相反的。
被刻意修饰得稀松平常。
表演呗。表演比现实更加现实。
不远不近处传来悠扬的舞曲,未经岁月打磨,中洲的音乐不怎么样,不过他们都不甚在意。
希拉看着他,那些声音忽然暗下来了。
他们的身影溶解在喧嚣的背景中,照样无法真正成为人群的一部分,不紧不慢地选择自己的路径,跳着自己的节奏。时间失去了她原有的意义,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就够了。
他们同步瞬移,跳了几步旋转到回廊拐角,再来一次,也就是在这里,这一切可以被解释作是杂耍戏。
周围的人渐渐停了,纷纷退后空出一段距离,只是在看他们。
他和它对视,渡鸦喙面具的弧弓将将贴到了他鼻尖上,若即若离得有些碍事。
他是如此美好,而希拉漫长的死亡中可以称之为美好的事物屈指可数。它的所有物并不算数。桑德兰是它黯淡的永生中最美好的东西。它倾身上前,用食指轻轻触及桑德兰的唇边,它们是有些苍白的浅紫罗兰色,略微有些肿,等待着被再次吞噬。那时神父在睡梦中不安地抖动了一下。希拉叹了口气,轻轻合上棺盖。
您不专心。
我知道。
在想什么?
在看着你。
桑德兰怀疑,或者说他知道,对方面具下展开了一个似有似无的微笑。厚重玻璃片下的眼睛蕴起反光,猩红半透明,这让它终于看起来有些像是它的实际年龄了。
一片羽毛掠过他们身边,随之缠绕旋转,当然是他的。片刻后,又笃定地遗失了。
今天你幻灭了么?
或许吧。他已经学会不先一步转移视线了。
一曲罢了,瘟疫医生抬手搭住他的肩,隔着一层丝布,指尖轻轻按住他的锁骨构造的凹槽,果不其然得到了一下转瞬即逝的轻颤。
“您觉得找到想要的了么。”
”您觉得呢。” 他不可置否。当然比起最末选项还是合宜一些。蛋白石月光打在宁静的湖面上,从中间晕开的暗灰金属色。
“与我觉得什么无关。” 瘟疫医生表示还是想听实话,crescit interea Roma Albae ruinis。[2]目前他已经逐渐演变成另外一种生物了,它不确定该对此欣慰还是惘然。
白面具暂时沉默,当现阶段的舞曲暂时告一段落,在离开前凑到它耳边轻轻低语,“谢谢你。”
为了这个?黑袍医生发出一声轻哼,注视着他从它视线边缘淡出。
第一幕后记
最近无限循环的权当是end score了:Jacob Miller et al., “Slipping Away”.
稍事休息,接下来想写写年轻的希拉,和桑德兰是如何无法质疑他曾经的选择的。
他和它在两座城市中游历和游离:独立战争前夕的纽约,共和国黄昏的罗马。偶尔相遇,却从未离开。
当然,莫忘了月落城🙂。第七天和魔界正式介入之后,该乱的都乱了。
[1] “Stranger, dance with me.” 希拉特意用英文说的。
[2] Meanwhile Rome grows on the ruins of Al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