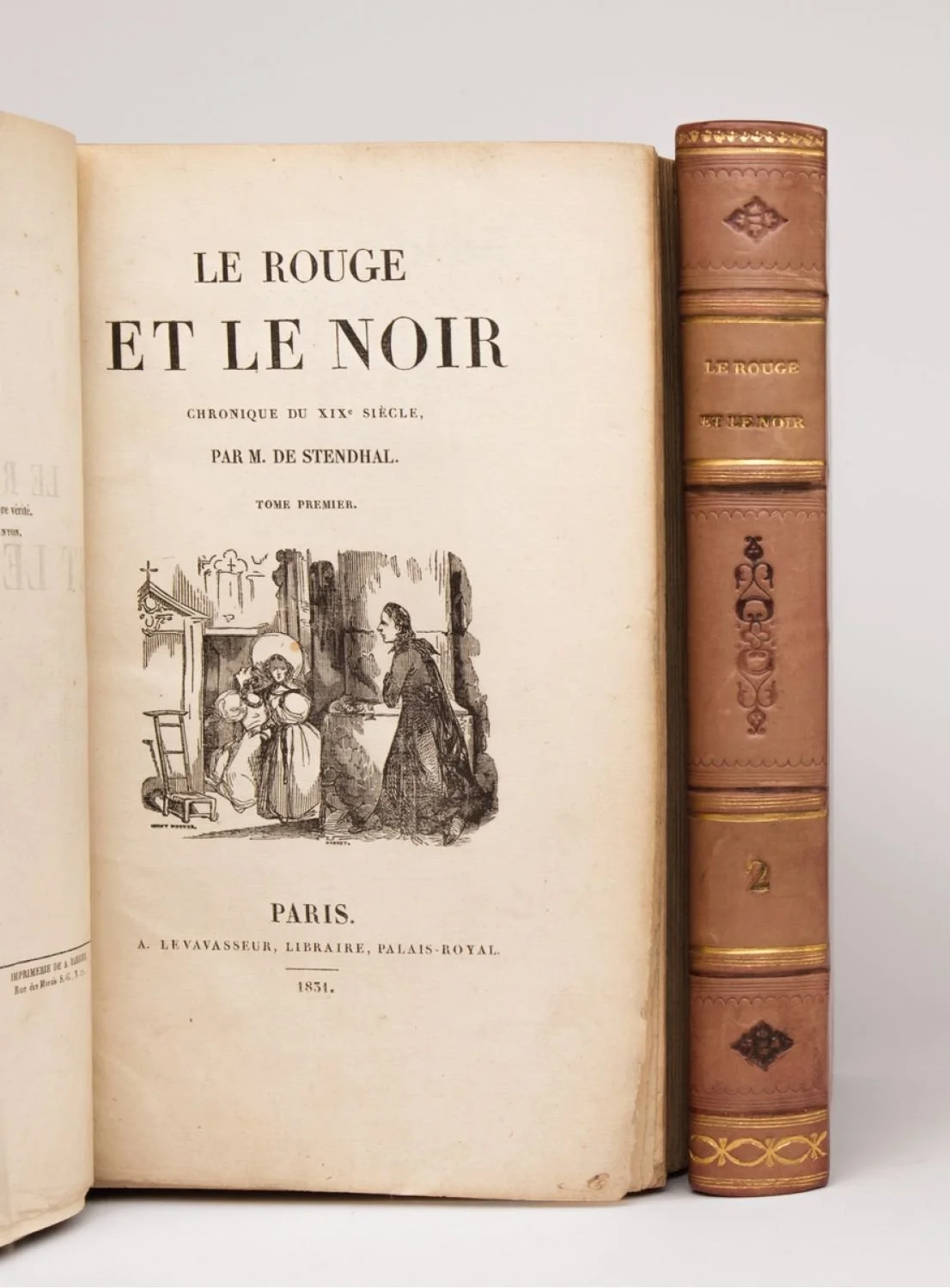Scorpiris Schemata 蝎鹫尾图式 第七章:第二次诞生
第七章
第二次诞生 No Longer Human
坐标 月落城东北翼,领主希拉·勒托里亚II的深红庄园,主人房。
Moonlit City, Northern Laetorii Territory, Crimson Hill of Lord Zillah Laetoria II, Master room.
...Ιρις...
桑德兰死后的第一个“早晨”突降得,几乎不可原谅得平静。
教科书中描述过咽喉刺痛,感官视野急剧放大的症状,却无法解释他目前的清醒,与精神的极度集中。
很好,他被精心清洗过,精神焕发。
桑德兰重新闭上僵硬的双眼,好像这样就可以屏蔽住自己作为神职人员,被它……转变为血族与血奴的既成事实。
四柱床帏间的动静明显没有避过一旁书桌前倚着的血族,他将单边眼镜放下瞬移上前,在桑德兰厌恶地避开前轻轻抚顺他额前的乱发,拖长声调恹恹地以命令式的语气道,
“啊,终于醒了,在你做出什么幼稚而无聊的尝试之前,我需要提醒你,第一,你的主严禁信徒以任何方式自裁。”
好像他还会接受我一样。桑德兰眼中闪过一丝压抑的恨意。
“第二,虽然接近下作,我想为了长远利益现在是我做出一些良性威胁的时候了。想想克里特侯爵,不对,如果军部的资料没有错的话,你还有一个…爱莉·冯·克里特,刚刚进入社交期的妹妹?”
桑德兰睁大眼睛,尖指甲抓破了重新换过的黑色丝绸床单。
“这么有精神?这要看你的合作态度了。”希拉冷冷地嘲笑,“噢不对,你已经不需要决定合作了。”
这句话成功引起了准备长期消极抵抗血奴契约的幼崽尖锐的目光,他回想起强制的手臂与按在他唇边手腕上的伤口,“为甚么——还不够么?”单单强行转变还不够么。
短暂的沉默,希拉最后说,“或许假以时日,你会真正明白。[1]”
桑德兰无声地看着它走到占了整面墙的嵌入式书柜的角落的酒柜,从高处取下一支墨绿色的酒瓶咬开瓶塞将液体倒入高脚杯中,室内立刻蔓延出他决计不会承认的甜香。
它缓缓地走过来,将高脚杯放在了床头立柜上,“神职人员的禁酒令,现在也该改改了。自便吧。“随后拖着黑袍掩上了门。[2]
...Ιρις...
工作台前,希拉把玩着银制手镯,指尖被烧灼着不觉。Well, well, well,他喜欢看着桑起床的样子,清醒前有一丝纯真与阴影,之后就开始戴上长年累月的那层善良无害的伪装了。
太久了,他回忆起桑脸颊不健康的红晕,脊柱上扬成可见骨节的优雅弧度,以及脖颈与胸腔轻轻的颤栗——纤细、易碎而微妙的脆弱!
不会再有了。
以及桑在身下时偶尔窥探出的满足、包容而宠溺的温柔眼神……思维又转回到神父惊骇,压抑而绝望的浅冰蓝,希拉在心中不可察觉地叹了口气。
希拉看到了桑灵魂中的灰色区域,从骨子里其实他也是一个猎手。确切地说,那种迂回巧妙布局的途径更类似于渔人(好像教廷几世纪中哪个红袍真正无辜一样),虽然他现在还没有认识到。
假以时日。希拉试图说服自己,直到楼上落地窗前海德里希那只愚蠢的蝙蝠又一次无谓地撞向玻璃上。可惜今天没法继续斗争了,虽然所有幼崽转变后都会无聊地来这么一出,以及算上极少数各个分支的信徒们的逆反期,希拉做好了长期斗争的心理准备。
瞬移到楼上,希拉不耐烦地打了个响指将窗前的装置打开,“好了小家伙,报上你的来意。“
“海德里希·冯·勒托里瑞斯V阁下对您在纳蒂亚女爵的婚礼上行使亲王仲裁权表示强烈的谴责,并保留将抗议记录在下议院档案的权利。[3]”蝙蝠颤颤巍巍地说,好像它意识到下一秒钟就将被无情拍死一样。
虽然希拉多次有这样的意图,但是考虑到傍晚的通讯不会仅限于来口头“强烈谴责”这么简单,还是懒洋洋地挥挥手示意,“继续。”
“海德里希·冯·勒托里瑞斯V阁下还说因为纳蒂亚小姐的事,弗拉德大公已经携诸多宠臣在斯克伊瑞斯议会上就反对魔党对波兰走廊的欧克拉翰虚无派的纵容态度持续,不间断地演讲三天了。[4]”
这倒是有趣的发展,鉴于斯克伊瑞斯的章程上的漏洞,在演说台上持续有人的状态理论上无法终止集会,在供血充足的情况下所有与会者都被无限时耽搁了,在暗自庆幸自己没有陷在那个鬼会议中,希拉还是问,“海德里希没有试图贿赂供宴厨房给…激情的演说家们断粮?”
“咳,海德里希 ·冯·勒托里瑞斯V阁下说这个对策被瓦萨里捷足先登了,现在迷你厨房的守卫比二战中莱茵兰的设防还严格。[5]”
“这样,让他们开得愉快。”希拉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让下一个轮班的雄辩家插入‘一个三足鼎立的欧克拉翰比两党连立的要讨人喜欢’,另外暂休期间给弗拉德递张小纸条,”他挥挥手召唤来羊皮纸与羽毛笔,写下“诚邀纳蒂亚VIII女爵邻日共进晚宴。——海德里希呈上。”
他将纸卷卷好,用指甲削下茶几上绑花束的一小截缎带,系了个漂亮的蝴蝶结。用这个满足弗拉德的拜金前情人估计足够了,反正纳蒂亚的目的是穿着昂贵婚纱让月落城的诸多未婚小姐们嫉妒得牙痒痒,新郎是谁并不重要。
不怕死凑在希拉肩头的传讯蝙蝠惨不忍睹地说,“月夫人是不会高兴的。“
希拉挑了挑眉,“你真的预习过自己的功课,不是吗?“
海德家的蝙蝠骄傲地回答,“那当然,我可是专业的传讯蝙蝠。”
在专业的传讯蝙蝠扑翅欲飞再一次撞向玻璃窗前,希拉准确地捏住了它的翅膀,“等等,顺便叫海德里希…”,他又召来帝国鹿下议院的代表名单,回忆了一下费尔南德Le Charme杂志中今年花少的排行,在其中两三个败类成串的贵族名字上不详地画了几个圈,默在了另一片羊皮纸上,“…把这几个青年俊杰介绍给亲爱的纳蒂亚小姐。”
看起来受到了精神创伤的蝙蝠点了点头,衔住了明显超重的名单一头撞上了落地窗。
希拉又弹了个响指将智障蝙蝠放了出去,生无可恋地按铃叫了个人类血奴将那三箱今天党内与领地内的公文从书房推下来。
虽然他想去看桑,虽然他希望读完水银期刊里那篇关于人体炼金的论文,然而次序还是要分轻重缓急。
当接近破晓希拉终于处理完普鲁士-波兰边界领地里拉比们的琐事,并给伊萨克爵士那篇“精心包裹的一派胡言”的论文写完回信,到底层去查看时,果然酒杯里的内容分毫未动。桑德兰无力地半靠在墙角,牛奶白的小手失神地抚过希拉新订的白色大理石石棺上的立体玫瑰雕面。
毕竟日久方长,他有中洲所有的时间和小神父耗。
...Ιρις...
失去了时间概念,虽然它偶尔隔天来匆匆查看后,高脚杯里换上新鲜的深红,又沉默着离开。
够了。整理完衣橱里的骨架,桑德兰闭上双眼。
他感觉到自己受到了侵犯,被打开,被暴尸在外,如同一本没有裁开页的书,被它尖利的指甲在每一道折痕上撕裂,暴露出丑恶的,崎岖的,不曾愈合的疤痕。没有痛感,而是一种僵直的麻木。
信理部所解释的症状永远是一样:首先是脊椎而上的降温,创口处的烫伤,咽喉刺痛,口干舌燥,心跳停止。然而这永远也无法解释他目前的状态,那种被强制的无力,全身燃烧之时渗入脊髓的冰冷。
抽象地灵魂出窍,桑德兰看到自己的意识浮在已死的身体上漠然俯视,嘴角裂开一个血红的、嘲讽的、冰冷的笑。
不,不再能够。他的灵魂已经被锁在了腐败的身体中。
甚至严格意义上,不再属于他的身体。
他首次对自己的皮肤感到深深的厌恶,他不想触碰自己,几乎不能直视自己的身体,他不禁想到少年时,许久以前……让侯爵与桑瑞妮夫人多么骄傲……那么多的爱……与神学院期间的晚祷——和现在他的污秽与肮脏。[6]
停下来,桑德兰,放过这些。他盯住茶几上摇曳的烛火,又闭上眼睛,试图逼自己回想一些霜白的画面离开这间猩红色调的牢笼,回想爱莎小时候星星样的小手, 在克里特府邸种满铃兰与山金车酊的花园中迎风摇坠。
被精心打理、找不到一点青苔的苍白大理石圣母像喷泉,源头浅口瓶缓缓流动,打落清澈的声音。
——幻听的水滴声响彻在信理部见习期间在中欧山地教区边界,空有圣力而断水的两个日夜。不,你不能喝黑巫师留下的水,毫无保障都是保守的陈述,明明知晓都是诅咒和毒。
肥皂泡轻柔地飘飞,爱莉以她不属于俗世的真挚而纯美的荣耀,拖拽着浅鹫尾色的羊腿袖罩裙与雪白的小围裙咯咯地笑着跑上前,挑起来将歪歪扭扭的淡金色山金车花环戴在了他的额前
——化作了荆棘,爱莉双眼流出两道红得发黑的血泪。
他笑着俯下身,在妹妹牛奶白的额前印下一个吻。
——薄唇向下划去,露出尖牙深深刺入了爱莉天鹅一样的锁骨间。爱莉发出一声虚弱的,被摁住的尖叫。
Genug! (够了!)
他又想起少年时期在为数不多的假期,午后在中欧典型的林间漫步。由于年轻时期对死亡这个概念的莫名吸引,曾经悄悄绕过切斯特与里尔克,带着清水与干净的软布到异教徒园林式的废弃公墓中,帮忙清理那些迷失的灵魂的墓碑与杂草。
缓步在青苔,扇形蕨类与凌乱得有着自己独特的秩序的石碑之间,看到不知名的墓志铭渐渐清晰,与熟悉的陌生人一闪而过的姓名,在一种怡人而使人深省的界面中获得短暂的,恬然的平静。[7]
——他伸手抹去下一个墓碑上的灰尘,渐渐显现的是,所谓的必然。
【Xandelaide Endris Valtin von Laetoria-Kret[8]】
【桑德莱德 恩得里斯 瓦尔汀 冯 勒托里亚-克里特】
【1716-1750】
回到眼前,桑德兰看着暗红色房间角落恶意地并排摆着的黑色与白色大理石石棺,预示了自己的未来,未来永恒的时间。
如果他一味任由事态发展的话。
他从未感觉过自己如此疏离,一切的感情似乎都死了,唯一还拖沓着的是残存的意识:希拉不会得到它想要的。
总是暂时的,他也明白。但这并不是停止抵抗,屈膝张开双腿放弃的理由。
[1] In der Zeit werden Sie verstehen. 直译是“In time, you will understand.“[2] 18世纪时天主教神职人员其实并不禁酒,希拉因为想到的是改革前的中世纪早期基督徒行为准则所以错认了。
[3] 勒托里亚亲王拥有“在亲王判定特定血族侵犯或将侵犯勒托里亚共同利益“时,跳过最高法院与帝国议会投票的处决权。亲王仲裁权包括所有勒托里亚的积极消极公民与贵族,历史上为希拉II的日常消遣清洗活动提供了正当理由。
[4] O’Ceallacháin Nihilists,简称N派,密党欧克拉翰族被北爱尔兰与西北普鲁士的自由党理想派, 波兰走廊偏向中立的虚无派与俄罗斯西部的社会党派系三分。
[5] 指第二次魔党与密党的主要冲突。
[6] 部分桑德兰的心理描写参考了1954年一名德国女记者匿名发表的 A Woman in Berlin,关于苏联占领期间对柏林女性的暴行。
[7] 原型是二战之后的波兰犹太人在森林中的坟地。
[8] 当双方都是高层贵族的时候,联姻之后有hyphening 女方姓氏的习惯。